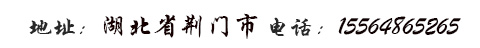作家地理杨志军十万嘛呢
|
只看白癜风的医生 http://m.39.net/pf/a_4342053.html 青海玉树 十万嘛呢 杨志军 4 妈妈高估了我,我不会骑马,哪儿也去不了。然而,就因为我不会骑马,我对骑马充满了兴趣。这是一个阴天,很凉很凉的秋风从雪山那边吹来,我的脸颊和手背立刻有了针刺的感觉。妈妈用勺子挖了一块酥油,让我搽在脸上手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解释不清楚,只是说:“抹上,抹上。”后来巴桑告诉我,涂抹酥油既可以防冻防裂,更是一种祝福吉祥安康的表示。因为,我就要骑马了,骑马跟放牧跟迁徙跟远行相关。对一个牧家男子,这是一个隆重的开端。妈妈为我在红马背上铺好马褥子,又架上光亮的马鞍和马镫。我走过去,扳住鞍头,踩着马镫就要上。鞍鞯顿时歪斜了,从马背上滑下来,我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妈妈过来扶我。我站起来,揉着屁股说:“怎么回事?”我和妈妈再次铺好马褥子,架起马鞍。妈妈迅速抓住了耷拉着的马肚带。我明白了,原来刚才我没有拴好马肚带。在我拴紧马肚带时,妈妈不停地用指头检测着松紧,最后说:“哦呀。”又把手伸到了马褥子下面,仔细摸了摸,摸出了一根小草枝。以后我知道,马褥子下面绝对不能有异物——草棍、石头什么的,它们会让马背磨出血。马感到疼痛就会跳,会把人从马背上掀下来。 我的骑马就这样开始了。最初是妈妈拉着马,让我在帐房门前绕圈子。渐渐地她就松开了,看着我在马背上紧张地扭来扭去。有一次脚脱了镫,妈妈过来,把我的脚塞进了马镫;还有一次缰绳掉在了地上,妈妈捡起来交给了我。就这样她放下手里的活,一直守护着我,差不多守护了两个小时,直到我腰酸腿疼得想下来。妈妈过来拉住了马笼头,我溜下马背,瘸着腿走进了帐房。妈妈跟进来,站在我身边,不停地念着嘛呢。我还算有灵性,在妈妈的保护下,学着骑了两天,就可以来去自如了。其实红马很老实,也是一匹训练有素的好走马,一开始之所以颠得我腰疼、腿疼、屁股疼,是因为我太僵硬,身体不能跟马的行进起伏保持一致。“妈妈,我学会骑马啦。”“巴桑,我学会骑马啦。”晚上,吃着均匀地撒了一层白糖的酸奶,我兴奋地说。妈妈和巴桑都笑了。妈妈的豁牙让她笑得尤其好看。 以后的几天里,我骑着马到处走。有一次我甚至走到了巴桑放牧的地方。巴桑正坐在草疙瘩上捻毛线,他一手从袖筒里抽取羊毛,一手旋转着木杆做的线砣,看我骑马走来,大声说:“扎西啦,你的马瘦啦。不能上午下午都骑,你得把吃草的时间留出来。这样吧,红马你留下让它吃草,黑马你骑回去。”黑马比红马高大,也显得没有红马老实。但是我居然顺顺当当骑回来了。妈妈老远看到了我,高兴地说:“哦呀,哦呀。” 很快过去了一个星期。明天,按照原定计划,巴桑家一大早就要搬迁,搬到相对避风暖和的冬窝子去。冬窝子在河谷地带,骑着马,赶着牛群和羊群,至少得走两天。也就是说,今天,县上的司机旦周必须来这里把我接回去。我们盼望了整整一天,旦周和那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始终杳无音信。晚上吃饭时,巴桑跟我商量:“这样的话你得跟我们走。”我说:“我要是走了,汽车来接时就找不到了。县上的人会知道我去了哪里吗?”巴桑摇摇头:“他们知道个什么?”“那怎么办?”我一脸焦忧,“不会是旦周把我忘了吧?”妈妈和巴桑用藏语说起来。巴桑愣怔着,片刻说:“只能这样啦。”之后又对我说,“你不要着急嘛,妈妈说啦,她会在这里守着你,帐房也不搬。我一个人把牛羊赶下去,牛羊不走不行啦,这里的草都吃光啦。”我松了一口气,又担忧地说:“如果我走了,你又不在,妈妈一个人怎么办?”巴桑说:“半个月以后我会向生产队请假来接妈妈,你放心,扎西啦。” 第二天一大早,巴桑骑着黑马,赶着牲畜走了,留下了三头奶牛和它们的牛犊,留下了大黑狗和红马。妈妈一如既然地忙这忙那,先烧好奶茶让我吃早饭,之后便去挤奶,收拾昨天晚上留下的牛粪和羊粪——把四散的羊粪蛋集中到羊粪堆上,把牛粪团成牛粪饼摊在草原上。前些日子摊下的牛粪饼已经半干,妈妈收拾到一起,垒成了牛粪墙。羊粪和牛粪都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快到中午时,妈妈背着木桶去河边背水。而我一如既往地骑上红马,朝远处走去。不同的是,我不再是信马由缰地溜达,而是为了期待,为了迎接——总觉得会在某个瞬间,看到那辆已经由草绿变成土黄的北京吉普,从地平线上疾驰而来。 5 但是几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草原的绿正在一天天减少,一坨坨的枯黄就像落地的云彩,毫无规则地洇染着。风越来越硬了,远处的雪山突然靠近了许多,能感觉到那种厚实的冰凉正在围堵而来。旦周的确把我忘了,就像那个从西宁带我来玉树的卡车司机达洛一样。不过达洛当天就想了起来,可是旦周,似乎再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他也像达洛一样喝醉了?可他不能天天喝醉吧?更有可能是忙,县上就那么一辆小车,他忙得焦头烂额,自然就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我的情绪很低落,有点想家,想我的亲人,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我可不可以骑马回县上?一想就觉得不可以,我不知道路怎么走,方向都搞不清,更重要的是远,骑马走多少天才能到达?再说马,骑走了怎么还给巴桑家?总不能撂到县上不管吧?他家可只有两匹马,除了骑乘,还要搬家。 妈妈一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叫着她给我起的名字“扎西”,更加周到地为我做吃做喝。这样过了两天,我的情绪又好起来,毕竟我年轻,牵挂的事不多也不沉。我安慰自己道:耐心等着吧,总会有人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不会就这样被人遗忘的。再说了,有一个对我这么好的藏族妈妈,我也舍不得离开。想着,突然就有些愧疚:我妈妈妈妈地叫着,却并没有把她当作真正的妈妈,而她是拿我当真正的儿子的。我也没有帮她干过活,就看着她整天忙来忙去。我说:“妈妈,今天我来挤奶。”妈妈不让,说什么都不让,紧紧抱着牛奶桶,不让我靠近它。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她说:“你男人是哩。”“那就让我帮你做牛粪饼吧?”妈妈也是死活不肯,还是那句话:“你男人是哩。”我明白了,我是男人,就应该干最重的活。每天的活里,去河边背水是最重的,那么大的木头水桶,妈妈背起来时,腰弯得几乎要趴下,额头差不多都能碰到地面上。妈妈背不动整桶水,每次只能背半桶。但是我刚拿起水桶,就又被妈妈抢走了:“你男人是哩。”难道只要是男人,就可以什么也不干吗? 很快我就知道妈妈的用意了,她找出一个线砣来,要让我像巴桑那样捻毛线,又从毡铺下抽出一块牛皮,再拿来一根钢针、一把剪刀,在我的腰里拃了拃,要我给自己缝一件皮围裙,还指着我的脚说:“靴子,你没有。”我有些不知所措,既没有学着捻毛线,也没有学着缝围裙和做靴子。妈妈很吃惊也很失望,似乎一个男人不学捻线缝纫是不可思议的。以后我会知道,草原上的家庭分工就是这样:最累的活比如挤奶、团牛粪饼、背水都是女人的,最细的活比如捻线、缝补、制衣都是男人的,但他们并没有专门的时间做这些,总是边放牧边做。当然男人还要打猎,主要是打危害牛羊的狼。瞧瞧妈妈,她居然为我翻出了一把短刀、一杆以羚羊角作前叉的枪。可是,妈妈,子弹呢?妈妈无奈地叹口气:怎么没有子弹?后来巴桑告诉我:用狼皮换来的子弹都交到公社去了,枪也应该交到公社去,但是他们没交,藏起来了,许多人都藏起来了。就算没有子弹,枪端在手里,狼也会害怕。草原上的狼多得数不清,光靠狗保护不了牲畜。 尽管没有子弹,我依然按照妈妈的愿望背起了枪,挎上了短刀。当我翻身上马,就要打马出发时,妈妈一颠一颠地跑来,把一个装着酥油糌粑的牛毛绳口袋挂在了马鞍上,又朝我挥挥手:去吧,去吧,是男人就应该这样。我以帐房为圆心,转了一大圈回来,仿佛打猎凯旋了一般。有一天,我果真打到了猎物:用烟熏火燎的办法,从洞穴里逼出一只肥胖的哈拉(旱獭),唆使大黑狗追上去咬住了它。妈妈看到死哈拉后,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回身跑进帐房,跪在佛堂前,颤颤抖抖地祈祷着什么,然后就是念诵嘛呢。我杀生了,妈妈在为死去的生灵超度。而我却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盘腿坐在毡铺上,大口喝着妈妈为我准备好的奶茶。今天的奶茶,放了太多的酥油。 有一次,我陪着妈妈去河边背水——虽然妈妈不让我替她背水,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沉甸甸的水桶抱起来放到她背上,而不是由她跪在地上,套上绳子,费力地爬起。走着,我看到了一摊晒得半干的野牦牛的粪,赶紧拾起来。妈妈立刻示意让我把牛粪扔掉。牛粪不是宝吗?怎么能扔掉?妈妈走到另一摊牛粪前,用脚踢得翻过来,等了片刻,才俯身拾起。她说:“这样拾,这样拾。”几年后我才明白,牛粪下面往往隐藏着瘴气,直接拾会把手熏肿,踢起来是为了散尽瘴气。一天,妈妈拿出一根抛石的绳子,对我说:“乌朵。”我高兴地接了过来。乌朵也叫抛子,我见巴桑使过,把鸡蛋大的石头放进皮兜,甩起来,在头顶转几圈,再把一头突然朝前松开,啪的一声响,石头就会飞出去,使劲的话能飞到百米之外。这是放牧的工具,能指挥畜群走东走西,能让离散的牛羊归群,还能抵御狼豹。我甩起了乌朵,天天甩,甩得胳膊都疼了。一次次的失败换来了最后的成功,我能甩出去几十米击中目标了。妈妈站在我身后看着,张开豁牙的嘴,呵呵地笑。我回头说:“妈妈,我可以放牧啦。”妈妈说:“哦呀。” 我和妈妈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不知不觉间,我没有了着急,觉得这里挺好,跟妈妈在一起,啥都学会了。还能看到野生动物:一闪而逝的藏羚羊、不怕人的野牦牛、喜欢奔跑的野马(藏野驴)。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孤狼蹲踞在不远处的草冈上,犹豫了片刻,骑马走了过去。在我端枪做出瞄准的样子后,孤狼回身就跑。我打马追了过去,看到它边跑边回头,消失在草原深处。我回到帐房里,给妈妈说起来。妈妈拿起一块肉骨头,出去丢给了大黑狗,回来说:“牛犊子,牛犊子。”我明白她的意思:狼盯上了我家的几只牛犊。 半个多月后,巴桑骑着黑马来了一趟,看我还没有被接走,匆匆吃了点东西就走了,说是生产队派不出人顶替他,牛羊都关在圈里,饿一天可以,饿两天不行,必须赶回去。他走时我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巴桑说:“二十天以后吧。”“这么长时间?”“冬宰就要开始啦,队长说跟往年一样,一定要超额完成公购畜。”巴桑的话又引起了我对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的兴趣,问道:“上交的多了,家里会有吃的?”“不多啦,今年能宰的牲畜本来就比往年少,再一超额,剩下的十个指头就能数过来啦。”“那怎么办?”巴桑呵呵一笑:“好办得很,妈妈天天念嘛呢,佛会保佑我们的。”我说:“哦——呀,原来是这样。” 我已经想好了,二十天以后,巴桑再来时,我要跟着去冬窝子。妈妈不能再在这里了,这里地势太高,天太冷,她的脸和手每天都冻得红通通的。此后,我天天巴望着的,已经不是旦周的小车,而是巴桑的黑马了。 6 奶豆腐 酥油茶 天气越来越冷了。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看到我裹着睡觉的皮袍上,还盖着妈妈的皮袍。怕我拒绝,妈妈总是在我睡着后给我盖上她的皮袍,而她自己却只穿着夹袍和盖着一块氆氇。我说:“妈妈,你不能这样,你也要睡觉,你晚上不冷啊?”妈妈笑一笑,不回答,只是更多地从外面搬进来一些干牛粪。有一次半夜醒来,我看到妈妈正在往炉子里加牛粪,才明白本来应该熄火的炉灶整个晚上都在燃烧,这在牧人家,是相当奢侈的,因为牛粪有限,而整个冬天是那么漫长,有半年多,天上只要飘下东西来,就一定是雪。这一年的雪来得有些晚,因为妈妈说:“才来。”我骑马走向飞雪,仰面朝天,让大朵大朵的雪花飘到我脸上,飘进我嘴里。草原一片皓白,大面积的起伏就像动荡的云雾,正在淹没而来。突然又晴了,太阳刺破了一切,金色和白色遥相呼应着,阳光和雪花同时飘洒。我打马跑起来。坚实的存在还是草原。 二十天过去了,巴桑没有来。我说:“妈妈,他怎么会不来呢?”妈妈用汉话吃力地表达着,我听了半天才明白,巴桑伤心够了才会来。“妈妈,他为什么要伤心?”妈妈的表达更加吃力了,但我的反应却快起来。妈妈说,那些被宰的牛羊都是巴桑看着长大长肥的,一个个都有名字,天天叫它们,跟它们说话,突然宰掉了,能不伤心?或许巴桑去了远处的寺院,去为那些死去的牲畜祈祷。我明白了,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有忧伤伴随着草原牧民。因为信仰让他们善良,让他们不忍心宰杀牲畜,但高寒带的草原不长庄稼,人不吃牛羊肉就无法生活,于是就有了节制,有了为着吃肉的悲哭。如果不是为了给城里人供应肉食,他们自己宰杀的牛羊很少很少,抠抠索索仅够半饱而已。我说:“那我们就等着巴桑伤心够了再来吧。就算他不来也没关系,我也是你的儿子。”妈妈笑得满脸开花:“哦呀,哦呀。” 但是没想到,说完这话没几天,我跟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就突然终结了,那辆土黄色的北京吉普带着加足马力的轰鸣出现在帐房前面。本来见汽车不叫的大黑狗这一次狂叫不止。我正在给红马刷毛,妈妈正在一边念嘛呢一边挤奶。旦周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说:“记者啦,走走走,快走。”好像压根就不存在他忘了我的事,好像本来说好就是今天他来接我。我不无诧异地望着旦周说:“你怎么来啦?”好像他不应该来接我,好像我已经不需要他了。很快我就知道,是远在西宁的父亲要我回去的,马上就要高考了,年的高考——“文革”后恢复起来的第一届国家高考来得猝不及防。希望我能上大学的父亲把电话打给了报社,报社又打给了玉树州,州上又打给了杂多县,县上这才想起,有那么一个记者来过这里。哪去了?哪去了?自然会问到旦周。旦周平静地问:“要我去把他接回来吗?”在他看来,忘记把记者接回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不就是在帐房里多住些日子吗?美死了他,饿了吃手抓,渴了喝奶茶,还可以在草原上到处溜达。 我说:“别急嘛,怎么能说走就走?”我走向直起腰来愣愣地望着汽车的妈妈。我说:“妈妈,你看,接我的车来了。”妈妈笑了笑,不过没有像往常那样张嘴露出豁牙。她放下奶桶,念着嘛呢走向帐房,捅开火炉烧奶茶,又端过来糌粑匣子和酥油碗。旦周进来,大大咧咧坐到毡铺说:“奶茶里多放点盐巴的要哩,喝了就走。”等妈妈双手捧给他奶茶,他不顾冷烫,几口喝得半浅,然后翘起指头拌起了糌粑。 我想,就因为我,妈妈没有去冬窝子,现在我要走了,却把她一个人丢在了这里。这里荒寒一片,没有别的人家,巴桑什么时候来接妈妈?我想,狼来了怎么办?仅靠大黑狗,一只狼可以对付,一群狼就很难说了。而狼已经盯上了这里,它们一定知道这里只有两个人,我走了,就只有妈妈了。妈妈,我不能走,也不想走,我不忍心丢下你。我问旦周,能不能过两天再走。旦周说:“你的爸爸要你回去,怎么还能过两天呢?你不能让我空跑一趟,我忙得很,没有时间再来接你。”我只好面向妈妈:妈妈,我要走了。 还没有吃完糌粑,旦周就站了起来,一副着急回去的样子。我提上了我的帆布包,望着妈妈。妈妈低头不看我,拿了经常给我装食物的牛毛绳口袋,几乎把糌粑匣子里的所有糌粑都装进去,又放了一大块酥油。她知道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却并不知道到底有多远,以为今后的漫长路途上就只有这酥油糌粑了。妈妈抱着鼓鼓的牛毛绳口袋塞到我怀里,突然抬起头来,把一小块捏在手心里的酥油抹在了我脸上,不停地念着:“唵嘛呢呗咪吽。”妈妈又在祝福我了。我走出帐房,走向红马,从脸上抠下一点酥油,抹到了它的额际上:“再见了红马,吉祥啊。”红马是知道的,把鼻子伸过来,在我怀里噗噗地吹着气。我走向大黑狗,同样给它抹了一点酥油:“再见了大黑狗,吉祥啊。”大黑狗站起来,舔着我的手。我拍拍它:“小心狼,保护好妈妈。”我走向这些日子给我奉献了那么多奶茶、那么多酥油和酸奶的三头奶牛,分别抹了一点酥油:“再见了牦母牛,吉祥啊。”奶牛和它们的牛犊都望着我,看我转身离去,一头奶牛长长地哞叫了一声。我走向妈妈,紧紧地抱住她,在她耳边小声说:“妈妈,我走了。”我好像只会说这句话。然后,在旦周的催促下,我走向了北京吉普。妈妈跟过来,突然说:“扎西啦,等一等。”我又转身回到她面前。 妈妈说:“扎西啦,我没有礼物送给你。我念了十万嘛呢,我把十万嘛呢送给你。扎西啦,你带上我的十万嘛呢,这辈子下辈子扎西德勒。”我吃惊极了,妈妈说的全是汉话,而且很流利,似乎她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一张口便水到渠成了。旦周显得比我更吃惊,看看我,又看看妈妈:“佛祖啊,这个老人怎么了?”又说,“嘛呢给了人家,你怎么办?” 念一个嘛呢就是念一句“六字真言”——唵嘛呢呗咪吽。十万嘛呢,妈妈会念多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何况她也不会对她念过的嘛呢有一个准确的记忆,“十万”只是一个概数,它代表所有,代表妈妈毕生的积累——她从小到大六十年或者七十年念诵过的所有的所有的嘛呢。念嘛呢就是积累功德,积累功德就能带来幸福——今生今世的安康与富足、往生来世的美好与吉祥。十万嘛呢,妈妈把今生的功德和来世的福运都送给了我,这样的礼物,代表世代相传的信仰,是超越一切物质、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馈赠,是妈妈生命的全部。 妈妈还在对我说着什么,而我已是泪流满面了。我扑腾一声跪下,磕了一个头:“妈妈,我会再来看你……” 7 回县城的路上,我一声不吭,想着跟妈妈相处的一个多月里,老人家的点点滴滴、一举一动,想着回来看她的日子:妈妈爱吃糖却舍不得吃,每天只能用指甲盖挑上四五粒白糖尝一尝,而端给我的酸奶碗里,每次都会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我要给她多多地带些糖,水果糖、牛奶糖、红糖、白糖。她没有袜子,总是光脚穿着靴子,我要给她带几双厚厚的软软的棉袜子。她每天都要梳头,把辫子整整齐齐盘在头顶,因为在她看来,披头散发是鬼的模样,可是梳子已经断了,只有半把,而且是缺了齿的半把。我要给她带一把好梳子,不,两把、三把。我还要给她带些蛋糕、面包、饼干、沙琪玛、江米条、月饼,因为妈妈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 然而我没有,我今生今世再也没去过杂多县的当曲草原,再也没见到妈妈。 我回到西宁时,离高考只有四天。紧张的复习之后,很快进入了考场。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尤其是数学,几乎一窍不通。我面对数学卷子,枯坐了半个小时,就提前退场了。退场前,我在一道题也没做的考卷上无奈地画了一个叉。那一年,“文革”结束不久,鉴于“文革”中有个叫张铁生的因交白卷而被“四人帮”吹捧为“反潮流英雄”的政治事件,上面规定,只要有一门考试交了白卷的考生,不管其他成绩考得如何,一律不予录取。我很幸运,面对我的数学考卷,阅卷老师认为:该考生虽然只画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叉,但它画在几何图上,可以看成是画错了的连线,而不能算作白卷。“十万嘛呢”保佑,阅卷老师给了我1分还是2分。因为语文、历史、地理考得还不错,我进入了大学录取的名单。 考试之后,我想着我的藏族妈妈,想回去看看,但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已经没有办法去玉树草原,去澜沧江的源头——杂多草原了。三月份开学,之后便是紧紧张张的四年学习时光,我跟许多在本省读大学的人一样,如饥似渴的读书和对个人前途的设计以及去北京上海看看的愿望占满了全部时间,也包括几个宝贵的假期,没有机会让我再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省报,在文艺部做一名整天待在办公室的编辑。不久我就向领导提出请求:去记者部当一名可以自由跑动的记者。因为文艺部缺少人手,拖了一年才被允许。到了记者部,又分配我在城市搞工业报道。我没有一天安心的,屡次提出我要做一名农牧记者,去条件比较艰苦的牧区草原。又拖了半年多,好不容易如愿,分配给我的任务却是紧急前往海北州采访。我在海北牧区待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再去玉树时,距我离开妈妈的日子已经七年了。冬天,有雪,路不好走,走了五天才到达玉树州的结古镇。从结古镇到杂多县城的路已被大雪覆盖,没有车辆去那里。我守着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等了半个月,等来的却是更大的雪。加上报社打电话催我回去,就只能放弃了。来年吧,夏天吧,遥远而荒寒的杂多县的当曲草原,我日思夜想的妈妈,想去看看怎么就这么难呢? 以后,我又三次去玉树,有一次甚至到达了杂多县城。是夏天,却没有人没有车带我去当曲草原寻找我的藏族妈妈。那时候的路依然很糟,车依然很少。有人说:“太远了,那里人少得很,又不固定,一年要搬四五次家,去了连糌粑都吃不上。”又有人说:“你说她的儿子叫巴桑?巴桑多了,光县委就有四个,有老巴桑、小巴桑、男巴桑、女巴桑。”还有人问:“是西边的当曲,还是南边的当曲?”我这才知道,当曲是条河,流域很长,有三四百公里,当曲草原指的是当曲流域,就更加辽远开阔了。我找到了已不再开车的旦周,他看上去已是中年奔老年的样子了,居然不认识我,更不记得当曲草原那个给他端过奶茶的老妈妈。也难怪,他天天开车送人,上面来的人多了,怎么会记得我呢?至于老妈妈,他见过的不计其数,所有老妈妈对他都一样:端给他奶茶,请他吃糌粑。逐水草而居的妈妈,我到哪里去找你? 离开杂多县时我想,妈妈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我问过的,只知道她在抱养巴桑时,已经有白头发了。有白头发的年龄至少也是四十多岁吧?我见到巴桑时他大约二十六七岁,以此推断,妈妈跟我在一起时应该是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我离开妈妈已经十多年了,老人家还在吗?草原上寒冷、缺氧,加上食物单一(常年累月仅有牛羊肉、奶制品、青稞糌粑而已),能活到八十多岁的牧民很少很少。 我把带给妈妈的礼物分成了几份,送给了几个在街上碰到的陌生的藏族妈妈,然后就搭顺车回去了。这次回到西宁,报社让我重返文艺部,我答应了。 若干年后的年,我带着十万嘛呢来到了青岛。妈妈的保佑一直陪伴着我,这样的陪伴不仅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一种真实不虚的改变:我不杀生,不吃肉,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追求温度和清洁、悲悯和敬畏,我也开始积攒我的嘛呢——每当我心绪宁静,或者回青海,去西藏,走进寺院,我都会默诵“六字真言”,祈祷福分,积累功德,每次积累的可能不多,个或者个,但我都会毫无保留地送给朋友或别人,哪怕他是带给我不幸的那个人,祝福他们的今天和以后乃至来世。这种靠虔诚和信仰日积月累的无价之宝,伴随着我心脉的跳动,是生命能够呈现的最美丽的花朵。接受我吧,青岛,我带来了最好的礼物,我时刻在为你祝福。我在你的胸壤里生根发芽,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当感恩和报答变作海洋的一部分,那种天赐的蔚蓝和辽阔的清透,便是我心里眼里的全部。 我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想过,去杂多县的当曲草原寻找我的藏族妈妈。 有一种恩情不可回报,因为它只想让你变成恩情的一部分,去面对别人,面对所有的所有的过往;有一种盛典没有痕迹,它给你的灵魂剪彩,使其变成人心的太阳、头脑的光亮;有一种思想不必表达,它就像骨子里的绽放,让人看到一个人的芬芳其实就是为了他人的劳忙;有一种思念无法消除,它跟生命同样重要,时刻滋养你生的健康和永远坚挺的理想。 从青藏高原播种,在黄海滩头开花;从世界屋脊起源,在大洋此岸成海。——我有一个妈妈,她代表孕成和哺育,代表缘起和萌发,她是永远的高海拔。 妈妈,其实我天天都能看到你,在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地下,梦里梦外,都有你慈祥的笑容、朴素的身影;妈妈,你是草原本身,给我营养,给我心跳,给我踏实走路、步步留印的能力;妈妈,你是雪山的凝望,用清亮的眼睛监督我的纯洁,让我在洗浴冰雪之光的同时获得脱胎换骨的力量;妈妈,你是阳光的注入,你让我从此有了热情,有了燃烧,有了曙色的烂漫、牛粪火的温暖;妈妈,你是“六字真言”的化身,你让我变作长流不息的慈悲之水,抒发善良者的感情,续写爱的文章,爱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还有蓝的天空、绿的地面;妈妈,你是来自天上的卓玛(度母),播撒甘露,让全部的日子都属于健康与乐观,属于爱与吉祥;妈妈,你是一棵大树,长在我的心田,你用永远的葳蕤印证着我的肥沃,让所有的人看我都是鸟语花香;妈妈,你是汪洋里的渡船,引领我闯过人世的风浪,一路向前,让我知道什么叫思想的桅杆、精神的风帆、信仰的航标灯。妈妈,其实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你,就在街头巷尾、十字路口、楼厦之间、绿树丛中,你朝我走来,我朝你走去,妈妈。 年11月21日 作 者 简介 杨志军,种过地,当过兵,上过大学,干过记者。出生在青海,成长在高原,四十年的高原生活让作者有说不完的“藏地”和“藏獒”。年《藏獒》收获了数以百万册的销售纪录,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随后三年中,《远去的藏獒》、《藏獒2》、《藏獒3》等相继问世,进一步将“藏獒热”推向了高潮。作者用灵动而遒劲的笔触描画出了一张独特的西藏文化版图。 收获微店 扫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pz/8929.html
- 上一篇文章: 亲子鉴定大概多少钱,需要哪些手续
- 下一篇文章: 儿童简笔画精选海洋动物鱼的绘画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