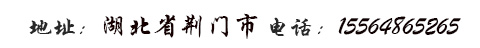为复仇她嫁给强奸犯,而强奸犯知道她知道
|
北京白癜风最好的治疗方法 http://www.wxlianghong.com/ 周末读书 破编有话说 INTRODUCE 《玉字》的故事是作家刘庆邦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刘庆邦巧妙改动了结局,让受气包成了复仇女神。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饱满,读罢,击节赞叹之余又头皮发麻。 玉字 作者:刘庆邦 电筒乱晃,鸡乱飞,狗乱叫。张庄的人手持棍棒、钉耙、铡刀等顺手家伙,呐喊着往村外跑。 玉字迎面走回来了。月光下,她低着头,头发不乱,衣服也没撕破,不像发生过什么事儿,只不过走路腿一拉一拉的,不似往日自然。 “吔,这不是玉字儿吗?”有人问。 玉字不抬头,也不说话,只管往村里走。快走到人群里,炽白的电筒光柱都照向她,有人喊了一声:“玉字儿!”她还是不应,走得更快些。一只相熟的狗迎上去,左右摇着尾巴,亲热地嗅她的手,她把狗头拨拉到一边,绕开狗走了。 人们有点泄气,有点疑惑,回过头找那报信的妇女。那老妇女急得赌咒,说她和玉字儿看完电影,手扯手回村,明明蹿上来两个戴一把捋帽子的男人,把玉字抱到高粱棵里去了,玉字儿还喊着“快救我”哩…… 张庄的人逮住邻村的那块高粱地撒开了气,他们抡开家伙,把正晒米的高粱杀的杀,砍的砍,不消一会儿,高粱乱七八糟倒了一地。 玉字回到家,爹娘哥嫂问她到底是咋着,她起先还是不吭,后来就突然哭起来,一上来就变了声,没个人腔。她躺在地上,身子乱滚,揪头发,摔头。嫂子刚要拢住她,她照嫂子肩头咬了一口。娘急得泪流满面,“字儿,字儿呀,别,别……你说话……”往地上一坐,也哭起来。玉字哭得背了气,头软软的,一边脸贴地,呼哧呼哧大口抽气,出气很短,浑身大抖,昏黄的煤油灯下,她闭着眼,脸煞白,披头散发。 这时屋里来了不少人,都是妇道人家,嘀嘀咕咕,乱出主意。有的说快请张先生扎一针,有的说快抓副疯药吃,人疯了再治就难了,李庄的李妮,出事后就疯了,看见男人就叫,就跑,后来跳了井。 玉字的哥黑着脸往外撵人,“没事儿,都走吧,死了干净!”玉字抖得更厉害,手脚痉挛得一抬一抬的。 白胡子张先生来了,低头看看玉字,冷不防跺了一个响脚,玉字顿时不抖了。他取出一支黑钢笔套,倒出一根针,在玉字鼻中隔上扎了一下,说:“把她抬到床上,喂点水,睡一觉就好了。” 玉字一觉睡了三天,不睁眼,不说话,滴水不进,一条被单蒙着头,直挺挺的,谁看见谁心里一寒。爹娘急得团团转,把玉字她姨娘请来了。一向被公认好嘴头子的姨娘坐在床头,叫了一百句“俺闺女”,比这比那,说了满屋子的好话,玉字不动。把玉字上中学时的女同学请来了,她们装出在学校时无拘无束的高兴样子,一替一句向玉字报告新鲜事儿,玉字毫无反应。庄上要好的闺女结伴来到床前,集体痛哭,玉字仍无动于衷…… 庄上的人都说,这闺女气性大得很,她不会起来了。接着就替玉字可惜,说她太抓强,太要巧,给她说了那么多婆家,都是别的闺女求之不得的好户,可她嫌这嫌那,一个也不应承。好比一朵鲜花,多少人转着圈儿要花大价钱买,她呢,把攥着舍不得撒手,这下好,掉在地上让猪给嚼了,一分钱也不值了。 有年轻人说,这事应该报告给乡里,派人来破案呀。庄上人说,破个屁,人烟这么稠,出事这么多,天高皇帝远的,公家的人管得过来吗!他们随随便便就拣来好多例子说明报案无用,除了丢人丢得远些,还要给乡里的治安员多搭几盒烟。 不是吗?马洼的赵本善,卖牛回来,被两个蒙脸人拉到高粱地里,搜去钱财不说,人也差点被勒死。谁见破案咧!李楼的喜莲,走了一趟姥娘家,人不见了,后来在一个桥洞里找到了,人都发了。谁见破案咧!他们设想,像玉字这样的事如果报给上头,公家人会说,是你水缸里的水少了?还是面盆里的面被挖走一瓢?好咧,不值啥,回去吧。设想罢,他们都笑了。 不知哪个嘴快的,趁赶集时把玉字的事跟乡治安员韩麻子说了,韩麻子骑一辆破自行车到张庄来了,一进庄就打听张玉字家在哪儿住。小孩子们看见韩麻子衣襟下别着“铁公鸡”,又怕又喜,争着带路。有的飞跑着去张家报信,好多大人也跟过来,想听听韩麻子怎样问案。 玉字的爹娘迎出来,却没让韩麻子进自家屋,把他让到玉字的大娘家去了。韩麻子刚把那事提了个苗梢儿,玉字娘就说:“哪有那事吔,这是谁拿着屎盆子往俺头上扣,俺闺女就是解了个小手,晚回来一会儿。”韩麻子也没深问,只说以后解小手注意点儿,就骑上车子,哗哗啦啦地走了。 第五天头上,玉字还没起来,年轻的生命被时间耗得差不多了,人瘦得脱了相,水灵灵的眼睛塌坑了,红润的脸庞变得灰白。娘拉出她的胳膊看,原来丰满洁白如藕节般的胳膊软溜溜的,已没力气蜷回去。似乎听见她喊娘,揭开被单看,她正咬牙,眼里汪满泪水。爹主张拿火锥来,撬开嘴灌她稀饭。娘给爹下跪,哭着说快给闺女准备个匣子吧。 哥来了,把爹娘推出去,掩了门,说:“咋着,当真想死吗?有刀有绳,有坑有井,哪尿窑子里死不了你,在这儿半死不活的干啥!”他从条几底下拿出一个玻璃瓶子,拧开盖儿,往玉字床前的地上一扽,一股浓烈的农药味即刻弥漫开来,“给,喝去吧,真有志气当时干啥咧,现在作死哩,要死早死……”玉字撩开被单,挣扎着要起来,由于太虚弱,胳膊咯噔一软,又倒在床上。 娘一头扑进来,骂着儿子狠心,掂起药瓶子扔进粪坑,乳白的药液嘟嘟地流出来。娘用铁锨把瓶子拍碎,随即去灶屋端来一碗稀饭喂玉字。玉字看了看娘,嘴角抽了几下,泪水滚在碗里。娘刚要把碗移开,她竟抓住碗,就着泪水把稀饭喝了。停了一会儿,娘又给她下了一碗软面条,玉字也吃下去了。 得了这两碗饭,玉字不睡了,摇摇晃晃要去梳头。娘抢着给她梳,怕她照镜子,被自己的样儿吓住,又灰心。玉字笑笑,顺从地坐在娘怀里,让娘梳。梳罢头,洗罢脸,玉字找出爹的一件棉袄来拆。她坐在薄团上,伸着腿,隔年的脏棉袄铺展在腿上,拿剪子尖儿一根一根把针脚挑断,揭开黑布片,露出灰白的棉絮。娘点了三根香,烧了几张黄表,跪在地上,身子扑得低低地磕头。 此后,玉字该吃就吃,该做就做,该睡就睡,跟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了。可是,庄上的人听不见她唱“谁不说俺家乡好”了,看不见她三天两头去镇上中学借小说了,她发起的“集体相亲协会”也散伙了。她走路低着头,两根长辫子直直地背在背上,成天没有一句话。出来进去,她不看人家,都是人家看她。 邻村的人打听:“那个张玉字死了吗?”听说没死觉得稀罕。庄上的人把这话学给玉字娘听,说:“不赖,别管咋,闺女活着就中。”玉字娘张罗着请人给闺女说媒,一盆水泼地上了,再也收不回来,不如挖个坑,给水一个去处。至于条件,就讲不起了,二婚头也可,进门就当娘也中,只要知道穿衣吃饭,半吊子也没啥。媒人、男人走马灯似的来了,那些半老的男人都是经过喜事的,进门眼睛乱瞅着找玉字,想拣这个便宜。一个穿了一身新衣的半吊子,提着两盒点心,两腿一抖一抖地也来了。 张庄的人在村口截住他,问他是不是想娶老婆,并说他这么聪明伶俐,肯定没有问题。他一喜,嘴咧到耳门。孩子们在大人的唆使下,拿污泥巴投他时,他顿时恼了,哇哇叫着追打孩子,结果把点心扔过去了。来求婚的,玉字娘都应承了,可玉字一个也不见,她说:“娘,想叫我死容易,不用这样……”娘赶紧把闺女搂住了。 玉字并不天天缩在家里,她隔三差五地去姨家走亲戚。张庄离她姨那庄不远,中间只隔一村,叫马寨。马寨东边有一条官路,玉字就走这条路。她走得很慢,走着走着坐下来歇上半天,再站起来慢慢走。 马寨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她在那条路上一出现,好多人都站在村头看。对她指指戳戳,有人说她是疯子,有人说她是不花钱的轧路机,还有人说得更下流,说她还想如何如何。 马寨的人拉马三来看。以前,有人把张玉字介绍给马三,人们估摸,凭马三的身条、长相、手艺和家底,张玉字会愿意。没想到见过一次面后,她嫌马三是宰羊的,身上有股膻味,还嫌他识字少,说话不照趟儿,没同意村里人想着,马三看见张玉字这样子,一定解气。可是,马三远远地看见她,笑笑,没说什么。 这天下午,玉字又往姨家走。秋天的田野里,庄稼差不多收完了,一两块没砍的玉米秆和棉花秆,被苦霜打得锈迹斑斑,一片发黑。秋风吹过,撕下一条条的玉米叶子飘向天空。她看见一个人挑着粪筐走过来,心里狂跳一阵,就迎上去。那人脚底迟疑了一下,干咳了两声,哼起梆子。玉字站在路中间看着他。快碰面时,那人唱的调门更高了,眼眯着,仿佛没看见玉字,身子晃着,肩上挑的筐左右悠达,眼看要走过去了。 “哎,你这个人,看着咋这么面熟哩!” “噢,——是你,” 那人站下了,“是的,面熟,面熟,是见过一面,俺高攀不上你,那次见面在哪儿呀,对了,在李庄河坡里,俺不中,文化浅,不会说话。你这是去哪儿?好,你去,你去,别耽误你的路……” 那人头上浸出汗珠,说着就要走。 “马三!”玉字喝住他,两眼直逼过去。“哎,噢——你还记着我的名字,不敢当,不敢当……听说你出了点儿事,我不信……” “少装样子,扒了皮我也认识你的骨头!” 马三的脸刷的苍白,腿一软,索索地抖起来,越抖越大,“啥?你说啥?你别吓唬人人人人,我马三三三三……” 玉字冷冷一笑,随即又把脸虎起来,厉声问道:“那个人是谁?” 马三浑身一激灵,反而不抖了,眼珠打了两个转,强硬起来,“你说啥?我不懂!你疯了,我不跟你说恁些!”说着溜路边走了。 玉字跟过去。马三架开膀子想跑。“马三,你慌啥,我又不是老虎,回来,咱俩商量点儿事。”说到后一句,声音低下去,口气有些软和。马三仿佛被一双无形而温柔的手拉了一把,脚下不由自主地定住了。 “我想好了,我——嫁给你!”这句又出乎马三的意料之外,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转过身看张玉字的脸和眼睛。玉字娇羞含嗔地看了他一眼,马三立时中了魔,眼直了,“这……” 玉字把头低了,眼也顺下去:“既然那样了,我有啥办法哩,往后就靠你了……”似有万千委屈不好出唇,啪哒啪哒掉下泪来。 马三慌了手脚:“中中,别哭,你一哭,我……反正那事找不到我头上,要不是可怜你……你等着,我马上托人说媒。咱先说好,这次可是你找着我的……日他个姐,我豁出去了……人对脾气,货对色……” 接下来的那一套送迎嫁娶和繁文缛节就不必细述了。玉字过门后,坐是坐相,站是站相,干活更是一把快手巧手。丈夫面前,温顺体贴,一应做妻子的义务做得很周全,口口声声爱说:“马三,你真坏。”马三初听,心里打沉,往后就听出相反的意思,心里浸出一股蜜来,越发鼓起男人的兴头。 公婆面前,她落落大方,既不为过去的事自卑、委琐,也不为对抗世人的眼光造作出高傲来,言语志量不与人同,公婆自然也得另眼相看。在村上,她把每一个人的辈分都悄悄记在心里,笑着称呼,那个准确和亲热,是别的新嫁娘过门一年也做不到的,令人喜得吃惊。村上辈高的人骂马三,说有福不在忙,算叫你这孩子逮住咧! 听了这话,马三对玉字好上加好,时常咧着嘴冲玉字傻笑。玉字去挑水,他上去把钩担要过来。玉字拉粪,他只在车上装了几锨,就让拉走。玉字嫌少,怕人家笑话。他再装,这次装得很高,玉字要拉走时,他却把架车把夺过来了。玉字在厨房烧锅,风箱把柴草灰吹出来,落了她一头。他让她歇着,自己一个大男人家去烧锅……玉字说:“我又不是神,谁让你供着!”马三说:“我……愿意。” 这晚要上床时,玉字坐在床沿哭了,肩膀一动一动的,抽泣得抬不起头来。马三慌了,问咋了,谁惹她了。她不说,只是哭。马三急得这边问,那边问,后来搂住她,掰她捂在脸上的手,“别哭中不中,我哪点对不住你,你说出来,我好改。” 玉字越发抽得紧,说:“马三,你……为啥不是第一个……” 马三像被人兜头打了一棍,先是头一懵,接着身上发凉,肚里发硬,手脚发软,一下子瘫坐在床上。 “我觉着对不起你!” 马三拳头在床帮咚地擂了一下,“你别说这中不中,再说我就死!”他脸色蜡黄,眼睛瞪得吓人,在咬牙切齿地骂人,骂得十分粗野。玉字还是哭。 马三睃了她一眼,看见她细细的腰,丰厚的背,雪白的脖颈,一切在哭时另换了一个样子,越发让人动心,一把强把玉字拉倒,“你咋知道是我?”口气有点调笑了。“你身上有股膻味,我想着就是你。”玉字不哭了,把马三扳着的肩头扭了几下。 “要不是我哩?——根本不是我,你别诬赖好人,宰羊的多着哩,我咋会干那事!” “是哩,马三是好人,谁也没有马三好,马三没起过坏心,下手没那么狠,没把人家掐死,马三没有摁住人家的脚,让狗日的——” 马三去捂她的嘴,她呼隆坐起来躲开,逼住马三,“我问你,你咋不卖羊肉了?” “你不是嫌有膻味吗?”“你知道我要嫁给你吗?” “知……知道。” “放狗屁,你做贼心虚!” 马三突然哭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央求玉字千万别再提那件事了,今后一切都听玉字的,叫往东不往西,这辈子报答不完,下辈子变牛变马接着报答。玉字说,这话多余,只要说出那人是谁,这事一笔勾销。 马三说:“你这不是往我心里捅刀子吗,要是成心不叫我活——”他抬起头往床帮上磕,玉字一把拽住,“哼,好大的志气!” 马三开始看着玉字的脸色过日子,走路脚不敢重,说话赔着小心,干一分钱的事也要先问过玉字,玉字说不管,他就不敢干,眼巴巴地看着玉字。他不再离开玉字,一会儿瞅不着她就急得团团转,瞅见了她就在她脸上乱找。吃饭时,他让玉字笑笑,玉字不笑他就不吃。玉字说笑不出来,他就当真不吃饭了。睡觉前,他打来热水,要给玉字洗脚,玉字不让他洗,他就呆站着不动。 玉字顶看不过他这样子,说:“你是咋啦?谁把你的脊梁骨抽了,你还算个男人吗!过去……哼!”马三眼挤巴挤巴又掉下泪来。玉字眼圈也红了,“三儿,别这样中不中,知道的说你对我好,不知道的还不知怎样说我辖治你哩,我真是那种毒心眼子的人吗!看你往后还做亏心事不做了!——那事你干过几回?” “啥事?” “又装迷瞪僧,你滚!” “咱不是说不提……”“我是不想提,忘不下咋办哩,我也管不住自己,有个鬼,老提着我。” 马三望着玉字的脸,“就那一回还不够我受的吗,要是再多一回,叫我咔叭儿一声就死。” “那个人哩?” “……” “你能保住他不害人吗?” 马三在屋里转了两个圈子,“豁啷”打开抽屉,抽出那把宰羊的尖刀,眼里放出凶光,“我去把那个狗熊捅了!” 玉字上前,一把将刀夺了,放回抽屉里,“咣当”把抽屉关上,“多大本事!”马三哼地往地上一蹲。玉字走过去,站得近近的,拨拉着他的头发,“该洗头了,我给你洗洗头,真是……” 马三顺势抱住她的腿,把她抱起来,嘴里胡乱喊着“金字儿,银字儿”,把她抱到床上去了。当晚,马三做了一个梦,惊醒了,大汗淋漓,他一声不吭,用胳膊触触,玉字脸朝外,还在他身边。 玉字说:“你发呓症了。” “我说啥了?”“乱七八糟,啥都说了,像是跟人吵架,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马三不吭了,黑暗中瞪着眼睛。停了一会儿,他慢慢把玉字拉转来,做着亲近的动作,却把两手移在玉字脖子上,越卡越紧。玉字一惊,“噗哧”笑了,“呀嘻嘻,你干吗胳肢我,痒痒死了。”她伸手在马三腋下抓了一把。马三触痒不禁,身子一滚,松开了手,“我试试你护痒不护。”又摸玉字的胸。玉字捉住他的手一摔,起身到另一头去了。 第二天,马三去镇上买化肥回来,一进屋就兴冲冲地说:“好事,好事。”玉字不问,看着他的脸。马三满脸通红,“人家跟你说好事,你一点也不高兴。”他赌气似的往椅子上一坐。 “啥事你说了吗?你会有啥好事!” “那家伙死了!” “谁?” “就是那家伙,他死了,汽车撞死的,头都轧碎了,活该!”马三使劲往地上呸了一口,又用脚使劲摩擦。 玉字嘴角牵一个微笑,“死了好。” 马三看见她那个笑了,“你不相信?” 玉字嗤了一下鼻子,“你不让我提他,谁叫你又提。” 马三说:“他死了,咱就心净了,可以安心过日子。” “谁不安心过日子了?我看是你自己。他是哪里人?姓啥名谁?” 马三又嗫嚅了,“反正死了,还问他干啥!” “既然死了,问问怕啥,我看你是要瞒我一辈子!” “我不瞒你,不瞒你,不……” 玉字身子一拧出去了。又回过头说:“锅里有饭,趁热吃吧,我一会儿回来刷锅。” 入了冬,交了九,大雪扑扑闪闪压地而来,把大平原上的小小村落压扁,盖严,到处一片白茫茫。这天午后,马三弄来一盆锯末,笼起一盆文火,沤出的缕缕紫烟驱着屋里的寒气。他在火盆边放一个小凳子,让玉字坐近些烤火,并抓一些玉米籽埋在热灰里,让它炸,“噗出”,炸开的玉米跳上来,白生生的一朵玉米花,喷香。玉字不吃,捧一本书在火边看。玉米花慢慢变黑。 马三不闲着,在屋当门就着雪光扎条帚。既然要“安心过日子”,就四季无闲时。他有力气,手也不笨,一团麻经子,一捆秫苗子,一会儿就在他手里生出条帚来,且式样不同,有鲤鱼甩尾,有野马分鬃,还有什么凤凰单展翅、双展翅。他宰羊的手艺更没说的,一头大公羊站着吃草,他一手抓住羊角,说是给羊挠挠痒,不知怎的,另一只手就把长苗子尖刀从羊耳门刺进去了。 玉字把书合上,压在胳膊下,单手托腮,看院子里大雪落地,看鸡们在大雪侵不到的柴垛下提着一只爪子呻吟,看雪团子在石榴树的枝条上滑脱,很快又粘上一层。看了一会儿,就啥也看不见了,只觉白色的模糊在流动,无休止地流动,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了。仿佛她自己也溶进这白色的模糊中,漂流走了,到那不知名的远方去了。待马三把她唤过神来,她眼角已挂了两滴泪。 “你咋啦?”马三问。她笑了笑,“不咋。”夸马三条帚扎得不赖。马三很得意,正要说“这不算啥,我还会用彩秫秆蔑儿编鸳鸯枕哩”,脸上突然僵住了,原来这时院子门口进来一个穿胶面雨衣的人,帽上肩上都是雪,那人一面说着雪真大,一面耸着肩膀抖擞身上的雪,在门坎上刮脚。 马三把手中的半个条帚往地上一扔,赶紧迎出去,说本村一个人的名字,问是不是找他,怎么走错门了,要带那人去找。说着两个人已碰了面。那个人笑着说:“不找别人,就找你。”斜着身子往屋里瞅。 马三拦住他,把他推了个反转,往外拥,手上使满了劲,嘴上却热情,“他家在东南角,走吧!”那人往后趔着身子,“哎,哎,你咋往外推我,咱弟兄俩,哎哎,弟妹哩?哎哟,你手劲好大!”扭回头嘻嘻地笑。 玉字心里一阵狂跳,手里的书“啪”地落在地上。两个人出了院子,马三一手抓着那人的胳膊,一手抓着后背的雨衣,往屋后领。这里是一片竹园,竹梢儿上压满了雪,地上的积雪也很新鲜,上面只有一溜羊蹄子印和鸡爪浅浅的印花。马三把那人一搡,搡倒在雪地上。 “狗日的,不是讲好的吗!你,还要多少?”那人站起来,嘻笑着:“要毬,大丈夫说话算话,一分钱也不要了,大冷天,不给烫壶酒喝!”这是一个瘦高个子,眼睛鼓着,下巴很尖,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马三,见马三激怒和恐惧的样子,觉得格外开心,一直嬉皮笑脸的。 “家里没酒了,明天我去找你,下馆子!” “有酒没酒没啥,不让进屋暖和一会儿?” “不让!” “你这货,真不够意思,要不是咱哥们……哼,你会恁舒坦!” “快滚,要不别怪我不客气!” 这时,玉字转过墙角过来了,两个人一下愣住了。玉字于大雪中,顶了一块红纱巾,脸上静静的,嗔着马三说:“哪儿来的客人?不进屋说话,让人站在雪地里,有你这样的吗?”瘦高个子眼里立即放光,“还是弟妹……”绕过马三,朝玉字走过去。 马三只好抢先凑近玉字说:“张娃欠他钱,让我帮着要,碍我啥事?”瘦高个子嘿嘿地笑:“对,对,老朋友帮帮忙嘛!”上去拍拍马三的肩膀,“哥们儿,中。” 来到屋里,玉字说:“你俩说话,我去炒菜。马三,你把酒筛筛,天冷,别喝凉的。”她没看那个瘦高个子,但她能觉出来,那人的目光无处不在,正在她身上乱刺。她到灶屋,马三跟过来,说这人是镇上一个剃头的,他们之间没啥交往,只不过见面认识,嘱玉字别炒菜太多,让他吃了还不如喂狗。玉字点头,说知道了,要他快去陪客。 菜炒好,酒筛热,瘦高个子弟妹弟妹地叫,让玉字过来一块儿坐着喝。马三沉着脸,说玉字滴酒不沾。那人离座要去拉玉字,马三伸手将他拉住,使劲一攥,他疼得直往一块儿缩。 玉字笑笑,大大方方过来,执壶,斟满一盅酒,一手端起,双手捧上,送到瘦高个子面前,“常听马三提起你,今天到家来,是看得起马三,我敬你一杯!”瘦高个子连忙站起,迭声说好,满瞅着玉字的脸,趁接酒时摸了一下玉字的手。玉字咕嘟起嘴,瞥了一眼马三,把埋怨和委屈的意思“说”明白了。马三“无意”中碰了一下桌子腿,“砰”的一响。 玉字随即又笑了,“喝,喝。”瘦高个子“呼啦”把酒喝干,就要回敬玉字一杯。玉字看着马三,说不会喝。马三说:“我替她喝。”把一杯酒往嘴里一撂,伸伸脖子咽下去了。瘦高个子不依,说不能替,“他是他,我是我,两个人不一样。”说着一脸猥亵相就出来了。马三眼里着了火,“我老婆不会喝,你干啥!”眼看弄僵了,玉字说:“好,我喝。”接过喝了半杯,看了看,把剩下的半杯也喝了。那人伸出大拇指,“好,弟妹够意思。” 一杯酒进口,玉字眼皮和双腮都红了。她似乎不胜酒力,眼皮一合一启,摇头微微一笑,露出白玉般的牙齿。结婚这么长时间,马三何曾见过玉字这种可人样子,又爱又恨,他夹一块鸡蛋喂玉字。玉字张嘴噙了,含混不清、娇声娇气地说:“还是三儿知道疼我,真是我男人……” 瘦高个子连连喝酒,酸辣甜菜都往肚子里收拾,酒从嘴角淌出来,流到脖子里,他借着酒力站起来,舌头硬硬地说:“他疼……疼你……小妹儿……该我了……”他一把拉了玉字的手腕子,夹了一片白菜帮子往玉字嘴里送。玉字顿时拉下脸子,扭过脸,求救似的看着马三。 马三霍地站起来,朝那个人腿上踢了一脚,那人一仄歪,松了玉字,红着眼珠子说:“马三,你……他妈的少来这一套,我说出来,谁也别想好过!”玉字做出不解的样子看着马三,眼里泪汪汪的,欲开口问,却把头低了,说:“你俩慢慢喝,我去烧点水。”起身出去了。 马三的脸阴得滴水,抓住酒壶不让那人喝了,压低声音说:“再胡唚老子宰了你!”那人笑着指马三:“你……不敢!”硬把酒壶抢到手,咕嘟咕嘟往嘴里灌。马三眼珠横了横,起身又拿出一瓶烈酒,把瓶盖啃开,给自己倒一杯,给那人也倒满,说一声干,谁不喝谁是孬种,先把自己的一杯喝了。 那人说好,也喝了。两人一连喝了好几个满杯,那人突然不喝了,眼往上翻着,脖颈伸向马三,头上下乱点:“哥们儿,我……不迷,你想把我灌醉,对不对?不中……我还要……轮也该轮到我了……” 他离了座,把酒杯和酒瓶扫落在地上,口里胡乱叫着“小妹儿小妹儿”,摇摇晃晃要出去。马三说:“等等。”回手在抽屉里抓了一把,往那人背上一捂,那人“啊”了两声,身子向上长了两下,像一个粮食布袋,直直地倒下,发出沉重的闷响。他嘴啃地,四肢往起支,想爬起来,结果胳膊腿儿抖得像琴弦一样,已支撑不起,嘴里喷出一股血,身子塌下去,头一扁,就不动了。 马三疯嚷起来:“就是他,我把他收拾了,咋着,跟宰只羊一样!”大声喊玉字。可没人应声。他旋即到灶屋,玉字不在。锁了门到几家邻居问过,也都说没见玉字。 马三便有些发毛,回家掖了些钱正准备逃走,听见门外有脚步声,知是玉字回来了,拉开门一看,一下呆住了,门口站着韩麻子,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人…… 图片来源:互联网 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 原创内容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zz/7307.html
- 上一篇文章: 穷与富的思维差距
- 下一篇文章: 房产投资中的ldquo穷人思维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