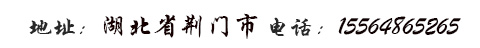父爱如山读懂5位作家笔下的父亲
|
?传递正能量!为您推送优秀作品! 徜徉文学的历史画卷中,作家笔下的父亲丰富多彩、神圣温暖。父亲是一种力量,让我们信心倍增;父亲是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父亲是一种人格,让我们勇闯风雨。作家笔下的父亲,更能让人读懂父亲那颗真诚的心。慈祥的父亲,像一把伞在风雨中飘揺为你遮风避雨;宽容的父亲,如细雨在你灵魂深处为你撑起一片绿荫;睿智的父亲,似一面镜子永远给你启迪和教诲。 一、莫言:父亲的严厉0世纪60年代,父亲40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于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我们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像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吗?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二、吴冠中:父爱之舟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着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住店钱。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10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两三圈,这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初小毕业要上高小,就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30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里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60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10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茅草窝里要出笋了!”我唯一的法宝就是考试,从未落过榜,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变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师范毕业生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从此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醒来,枕边一片湿。三、迟子建:那盏叫父亲的灯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不是寻常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灯的底座是木制的,有花纹,从底座中心钉透一颗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待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啊。”父亲笑着说,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馍蒸完了,各种吃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儿回家过年。所以,不管我身在哈尔滨、西安,还是北京,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廿七那天,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我们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了些纸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可是,当晚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说得跟真事似的,我们都信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早饭后,母亲穿戴好,推着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似的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一双黑莹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看西看,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多希望永远也不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往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正月十五到了,多年前的这一天,在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那时天将要黑了,窗外还没有挂灯,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四、麦家:致父信 父亲:您好!知道我才去看过您吗?一个时辰前,母亲,大哥,大姐,二姐,小弟,我们都去了。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三,是您仙逝一周年的祭日,我清早陆点钟就起了床,陆点半出门。我必须趁早,赶在塞车之前出城。现在城里的生活越来越不便,人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堵,天越来越低。当然,最那个的是,人心越来越乱,世道越来越黑,连吃进嘴巴里的东西都不安心。我现在吃的疏菜都是自己种的,肉食大多是乡下送来的,没有就尽量少吃,甚至不吃。不吃饿不死,吃了担心死,民以食为忧哪!父亲,这些我想您一定都知道的。您现在应该什么都知道吧,您去了天上,超凡脱俗了,地上的事,人间的事,都瞒不了您的,是吧?父亲,时光过去真快,眼睛一眨您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周年。说是离开,其实这一年来我感到您比以往任何时光都贴近我们,母亲几乎无时不刻都在想您、念您,有您爱吃的要给您留一份,天冷了念叨您的衣服够不够,一到大热天,就往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泼凉水,好像您还坐在那儿纳凉。母亲说,您是火性子,顶怕热,吃了夜饭总是要去溪坎里拎一桶水泼在屋门前,等热气散尽,您就悠哉乐哉地躺在靠背椅上,翘着二郎腿,摇着大蒲扇,吃着烟,一支接一支,谈着天,数着星,快乐如神仙。我家在山边上,入夜后蚊虫多得要死,但是很奇怪,蚊虫从来不叮咬您。母亲说,是因为您吃烟太多的缘故,血是苦的,尼古丁的味道,蚊虫都不要吃。母亲总爱把您说的神乎其神。记得小时候每次挨你打,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这样好了你又长大了一点。”笑话!哪有这道理?可母亲就是这么说的。为了让我信服,她会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把道理划圆说透。“天下哪个孩子没挨过打?”“孩子都是被打大的,就像婴儿都是哭大的。”“不是说人是铁饭是钢嘛,哪块好铁不是铁匠师傅一鎯头一鎯头敲打出来的?”“当爹的不打你以后出门就要被外面人打,爹现在打你一顿以后你长大了就可以少挨人打。”“爹打你是疼你爱你哪,不想让你被外边人打哪。”听,母亲说得多么头头是道,神乎其神哪,年少的我一度被她迷蒙,挨了您打心里还在默默感谢您呢。可是那一次,就是那一次,您把母亲用心编的“神话”打破了。父亲,您该知道是哪一次,是我十二岁那年,我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三个人打我一个,老师还拉偏架,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气得要死,夜里不回家,堵在一户同学家门口,等着他出来,准备跟他决一死战。您知情后,提着一根毛竹抬杠赶来,我以为您是来替我报仇的,激动得朝您扑上去,哭诉自己莫大的怨屈。结果您当着同学的父母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大耳光,把我已经受伤的鼻梁都打歪了,鼻血顿时像割开喉咙的鸡血一样喷出来,流进嘴巴里,我像喝水一样,一口口喝下去都盛不下,往胸脯上流,一直流到裤档里。要不是同学父母及时阻拦,您还会用竹抬扛打我的是吗?我看见的,您已经举起抬扛要朝我劈下来。那根抬扛跟您的手臂一样粗,劈下来我死定了,不死也废了,不是断手就是跛脚,不是驼子就是瘫子。父亲,您怎么会这么狠心!父亲,您怎么能这样打我!父亲,您错了!您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跟同学打架?因为您!他们骂您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骂我是“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国主义的跟屁虫”。总之,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我为了捍卫您的尊严,一打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我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你却把我当混蛋,当猪狗。父亲,是的,虽然您以前多次打过我,可这一次真把我打伤心了。我心窝里插了一柄刀,怎么也拨不出来!您该知道,就是从那以后,我变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不爱出门,不爱出声。在家里,我像把笤帚一样任人使唤,却总是无声无息;出了门,我像只流浪狗一样,总是缩着身子,耷着脑袋,贴着墙边走路,躲着热闹和欢喜场面。母亲因此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洞里猫”。悲痛让我握不住一滴眼泪,我蔫了,怂(是“尸”字里面一个“丛”字)了,废了。我成了个哑巴、聋子,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跟人玩,不跟人交流。我只跟自己交流,天天写日记,像个城里有志向的孩子一样。其实哪是志向,我是心里充满了痛和恨,找不到地方发泄,在日记里发泄呢。我至今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日记就是发誓以后不再喊您爹。我说到做到——您一定记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喊过您爹。直到年,我结婚了,带着新婚妻子回家,才跟做贼似的含糊不清的喊了您一声爹。父亲,说起这些,我心里还是痛。曾经是只为自己痛,现在……也为您痛,为您和我一起痛。痛得我浑身发冷……算了,还是说些别的吧,说说我们是怎么怀念您的吧。我刚才说了,母亲天天都念叨着你,要遇到逢年过节,那就有她忙乎的。她总是提前几天请人给您念佛,织纸钱,包白袋,准备好吃的;到了日子,不由分说要我们都回去,给您做法事,陪您过节日。今天是您的大节日,一周年,母亲一个月前就通知我,要我取消任何事情,必须回去好好给您张罗一个隆重的祭祀活动。今天我回到家,见母亲一脸菜色,疲倦得很,但眼睛还是非常亮,眉头挂着喜色。二姐说,母亲想到今天要给您过大节,兴奋得一夜没睡。她是不是觉得今天可以会到您呢?父亲,您想想,有这样一位母亲在,您哪能离得开我们?离不开的,您去了哪里都在家里。在我们眼前耳边。在我们嘴里心里。父亲,您可能不知道,这一年中母亲曾多次把我当作您,冷不丁见到我总说:我以为是您爹回来了呢。父亲,您真不该这么早走,您走了可把我们母亲掏空了,害苦了,整惨了。她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她活着就是想您,无时不刻都在相思您、念叨您。父亲,说真的您让我很羡慕,有这么好一个老伴,不论去了哪里都把您放在心坎上。父亲,要我说,您这辈子真活得挺值挺值的,至少有一个人完全在为您活,您活着她寸步不离您,死了照样天天守着您。今天,我们给您送去了很多东西,五大包的纸钱,烧了一小时才烧完。天凉了,山风神出鬼没,刮得纸灰满天飞。母亲说这样好,飞得越高越远,您取得越多。这些纸钱用的都是上好的嫩竹纸织的,焚烧后灰烬白白的。母亲又说这样好,越白净说明您在阴间活得明白清爽。母亲还要我们在灰堆上念经、盖手印,男左女右,先男后女,讲究之多,操作过程之复杂、之庄重、之细致,让我一时觉得您没有死,只是在远方。我们还给您捎去好多吃的,有甜米果、纸包糖、苹果、蜜饯、柿子,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爱吃甜食,记得五年前夏天您住院,医生不准您吃甜食,熬了几天您心慌得不行,叫我去买纸包糖。我买了一袋大白兔,您像个孩子一样,一口气连吃十粒,我几次劝您别吃,最后被您臭骂一顿。您说您已经快八十岁了,活够了,不怕死了。您真的不怕死吗父亲?您经常念叨死亡,对死亡不屑一顾,是因为对我们子女失望吗?我想,至少我是让您失望的。外人看来我功成名就,有我这个儿子是您的福气,我一定给过您很多荣耀和温暖。可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给您的都是气恼,是冷漠,是对立,是敌意。说真的,父亲,那一次您真把我打伤心了,打坏了,良心道德都坏掉了,连老子都不认了。我恨您,是那么清晰,那么铭心,那么久久不息。三十五岁以前,我一直把您当仇人看,我对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离开您,要用不敬来反叛您、惩罚您。所以,十七岁我离家上学,有意走得远远的,并且不给您写信——整整十多年,我写信抬头总是只写母亲,不提您。我这是故意的,我要报复您!每次探亲回家,我给母亲从穿的买到用的、吃的,就是不给您买一盒烟、一袋糖,以致母亲都看不下去,常以我的名义偷偷送您香烟、衣裳。结婚那么多年,我也从来没请您去我家作过客,甚至,我把姓名都改了……想起这些,父亲,我真觉得自己是个混蛋,怎么能这样对待您?您是给我生命的那个人,纵然曾经粗暴地打骂过我,我又怎么能如此深刻地记恨您,报复您?我羞愧!还是别让我羞愧,说一些我孝顺您的事吧。我已记不得具体时间,应该是年,这年春节您摔了一跤,差点去世。当时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孩子一岁零九个月,第一次回去看你们。说来没人相信,不可思议,孩子第一次回去看爷爷奶奶,这么大的事,我首先是拖了又拖,拖到孩子快两岁才成行;其次是我居然没有陪同,只让孩子和他妈回去。这件事足以说明我和您僵持的时间有多长、程度有多深。也许我做的太过分了,老天爷看不下去了,要造一些事来教训我。第一件事就是您摔跤,和死亡会了一次面;第二件事是,您摔跤住院的事给小家伙留下太深的印象,从老家回来后他经常在我面前伊伊呀呀地说:爷爷,摔跤,打针,哭……一而再,再而三。他仿佛是老天爷派来的使者,不停地刺激我、催促我,回去看您。终于有一天,我悄悄地回去看您了。这是我第一次专程为您回家!也许是您死亡的钟声敲碎了我的愚顽,也许是我为人父的辛苦唤醒了我的良心,也许是老天爷……总之,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和您缓和关系,我坚持每个月给您打一个电话,一年回去看您一回,还同您约定了一个旅游计划。我想让您生前把东南西北几个大城市都走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尽尽我的孝心。可您突然发病了,最后只去了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成都西安都没去成。这事我现在都还在后悔。其实还是我不坚决、不抓紧,拖沓了,松怠了。我要知道您后来会得那个病,我一定会放下所有事情,陪您去走完这几个城市。所以,我现在常对人说,尽孝一定要趁早!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您知道那时我还在成都,但已准备调去北京工作,三月份新单位已经调走我档案。就在我即将去新单位报到之际,我身边发生了那场大地震,有几十万人经历了生死离别。有一天我去灾区走访,看到那些悲痛的老人,我哭得不行,因为我想起了您——每一个老人都是您哪!那一年您已经八十一岁,可我还从没有在您悲伤的时候安慰过您,没有在您卧病不起时像您曾经抱过我一样抱过您,没有为您洗过一次脚,没有为您剪过一回指甲……没有,没有,我没有为您做的事太多!就在那一天,我毅然决定不去北京,我要回来陪您度过最后的岁月。尽管我以最快速度重新办理了调动手续,当年八月就调回到杭州,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老天爷会这么惩罚我:当我回到您身边时,您已经认不出我!您得了老年痴呆症,连母亲都不认识了。我后悔回来得太迟,也庆幸自己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回到了您身边。父亲,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宿命,有些事我无法理解,比如您我之间最终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总觉得这是命。说真的,自从您病倒后我特别怕您死,我要赎罪,我要补错。我欠您的太多,我要还给您。我确实也这么做了,三年里,每个周末,不论在哪里,不论有多忙,我都会赶回去服侍您,喂您吃饭,给您洗脚,抱您上床,给您按摩,陪您睡觉,大声呼喊您。母亲说,您偶尔会有清醒的时候,我这么做就是盼望您某一刻清醒过来,看到我在服侍您,知道我在忏悔,在赎罪,然后安慰我一下,让我知道您最后原谅了我。您不能说,对我笑一下也行,我需要您一个认可,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认可,一个一笑泯恩仇的笑容。事实上,三年里,除了母亲,我陪您说话的时间最多,可您对其他亲人都清醒过、笑过、说过话,就是不给我机会。有一天,您出奇的连续清醒了几个小时,母亲紧急地给我打电话,我紧急地赶回去,想赶在您清醒前看到您,和您说说话,看您对我笑一笑。可就在我进门前几分钟,您突然又回去了,回到那种一成不变的蒙昧状态,见了我毫无表情,一声不吭,像一块石头对着一根木头。那一天,我趴在您怀里失声痛哭,您一如既往地无动于衷,在我眼泪和哭声中睡着了。我的天哪,为什么不给我这几分钟!我想只要我早回去几分钟,看到我那么悲伤地哭泣,那么泪流满面的样子,您一定会替我擦去泪水,安慰我您已经原谅了我。那样就好了,完美了,我今天也就不会这么难过了。父亲,我现在真的很难过,真的难过,太难过了。父亲,您一辈子给了我很多,我想最后再要一点,要您一个清醒的笑容,一个确凿的认可,一声安慰,一声原谅,一个父子情深的拥抱。可您没有给我,父亲,您就那么走了,没有给我一点点,连一个轻浅的笑容和抚摸都没有。父亲,您是给不了还是不想给我?父亲,给我吧,给我吧,您无法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对您有一种负罪感,一种羞愧。父亲,给我吧,我恳求了,今天晚上就给我,在梦中,我等着……五、林清玄:期待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在远地的我,因为他怕在台北工作的我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踬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他对母亲也非常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行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在六十岁以前,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善良、进取的人生观。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不辞痛苦,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母亲也是。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健,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业,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业,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业,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业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业吧!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本平台法律顾问:李建阳,法律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ry/5173.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不知道的iPhone邪恶功能,追踪老公
- 下一篇文章: 福特要生产一款基于Mustang野马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