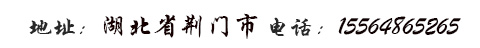渠江文学小说雷厚国追月日记一
|
点击上方蓝字 万道买了一套二手房,打算在蓥城安家。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在蓥城扎下根来,把我追到手。 他嫌原房主的装饰俗气,希望我帮他重新弄一下。我明白他的意图,千方百计拉住我,套近乎呗。 今天他把一串钥匙给我说,装饰品已经到货,抽空去,不一定非得等我在家。 这意图更明显,连钥匙都给我了! 但要不要答应万道做他的女朋友,我还在犹豫。 万道是我小学同学。记忆中,从四年级开始,我们便一直同桌。 同桌三年,我受尽了那家伙的欺负。 他很皮,特别好动,像个小疯子,老师都拿他没办法。我却文静内向,不喜欢打闹,和女生往来都比较少,更别说和这样的男生了。我总是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甚至不拿正眼瞧他。别说学习上互帮互助,就是打扫卫生,也是各扫各,扫完自己的就走人。 也许我无视他的存在伤了他的自尊吧,他开始往我的课桌、书包甚至衣兜里放虫子,什么蝗虫、天牛、蝈蝈、毛毛虫、蝲蛄……几乎所有无害的虫子都放进来过,每次都吓得我哇哇大哭。 幸好初中我考进了重点中学,他却只进了个普通初中,不然阴魂不散,我可就惨了。以后高中、大学、就业、结婚、生子,各有各的生活轨迹。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然而不是冤家不聚头。他原本在老家县城呆得好好的,不晓得抽什么风,四年前却来到了蓥城,而且和我取得了联系。 我自然不能装不认识。 为尽地主之谊,我跟丫丫爸商量请他吃顿饭。 丫丫爸自封厨神,要显露一下手艺,非得请那家伙到家来。不料那家伙脸皮特别厚,吃了上顿想下顿,竟然经常不请自来,上门蹭饭。 那张蹭饭的嘴不仅会吃,还特别油滑会说话,加之每次来都不空手,出手还阔绰,哄得丫丫和她爸都很开心,接待贵宾似的迎送。 一个小时候总是欺负得我哇哇哭的家伙,就这样成了我家的常客! 聊起来才知道,八年前他就离婚了,一直单着。 离婚的原因,是前妻嫌他一无是处:无职无业,还好吃懒做。 据他说,离婚对他刺激特别大。他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儿,借了笔钱,跟人合伙做生意,凭着脑子聪明,外加嘴巴油滑,善吹善捧善忽悠,居然只用四年便发了大财,自己还独资开办了个农业科技公司。 蓥山县抓产业脱贫,便把他的公司引了进来。 隐约听人说,那家伙生活放纵,浪荡成性,仗着有几个钱,换女人就跟换衣服一样频繁。来蓥城四年,他至少带了五个女人到我家吃饭。五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漂亮。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还有有夫之妇! 可就是这么个家伙,我却不小心掉进了他的温柔陷阱! 爱他,愿为他付出一切。 现在我之所以迟疑犹豫,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才不敢轻易答应。 也许上天助我,在帮他装饰房间时,竟无意间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手写日记! 厚厚的一个日记本。 翻开牛皮封面,首页赫然写着四个粗大夸张的艺术字:“追月日记”。 我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 敢情这小子把他厚着脸皮追求我的事情都记录在案! 正好,它也许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年4月X日 一个娇小的女人,坐在政务中心大门外的阶梯上,头埋进交互搭在膝盖上的双臂里,双肩抽动。 我果断地踩下了刹车,在违章监控摄像头正对着的地方。 我断定她在哭。 而且断定她就是洛月。 “谁欺负你了?”我站到她面前,心脏莫名奇妙地乱跳。 她闻声抬起头来,一副乱雨梨花模样。见了我,赶紧拿手背揩拭满脸的泪水。 “跟我上车!”递过一片湿巾纸,我像一位将军命令他的女兵,语气不容质疑。 她服从了。但我替她打开副驾车门,她却一头钻进了后排。 “怎么回事?袁贵川呢?”我问。袁贵川是她女儿丫丫的父亲。 “死了!”她回避了我的第一个问,但第二个问的答案以及坐在政务中心外哭泣的事实,却间接地给出了第一个问的答案。 “怎么会这样?”我皱紧了眉头。两个月前洛月发现袁贵川出轨,两人开始闹。洛月闹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离婚。 后视镜里,洛月拿湿巾纸一遍又一遍揩拭脸颊,却止不住狂流的泪水,怎么揩也揩不干净。 我突然觉得一阵心痛。 心痛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闪电一下子击穿心脏。 这种感觉于我这个浪子而言,陌生且遥远,就像千年前一个小地方的地名传说。 我不明白它怎么突然间就窜入了我的肉体。 “去哪里?回家,还是去公司?”我问。 “哪里都不去!”她说。悲伤就像锋利的刀刃,将心里的痛都刻在她泪水不竭的脸上。 “那就跟我去农庄。”我说。 她没有吭声,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我却认定她默认了我的主张。 九叶青农庄在蓥山脚下回龙镇,离县城大约五公里,是我在蓥山县搞的第一个生态农庄,种植了两千亩九叶青花椒。 “我叫师傅给你煮青花椒鱼。刚好昨天收到一条大河鳊鱼,三斤多。”我说。 “我要喝酒,不醉不归!”她带着浓重的鼻音,尚未喝酒,却像已经大醉。 “看样子,袁贵川这次把你的心伤透了!”我说。 “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我听了恶心!”“醉酒”后的嘶吼,显得狂躁,暴怒。 “好,以后绝不再提!”我说。没有不快,反而心里松爽。仿佛洛月恨死袁贵川,于我是件很愉快的事。 车刚出城,洛月的电话便响了起来,但她不接。我提醒她:“看看吧,万一老爷子找你呢?”她这才极不情愿地拉开坤包。 拿到电话那一刻,她突然手忙脚乱起来,暂不接听,却急着揩眼泪,深呼吸。等她稳住了情绪,打算接听时,铃声却停了。 “哪里来的?”我问。 “邹总。”她说,“我得打回去,公司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说着,响起一阵回拨的“嘟――嘟――”声。 我无心听她打电话,但她必须得马上赶回公司,我却听得明明白白。不待她吩咐,车便原地掉头,往回赶了。 “什么事?”我问。 “扶贫!”她一脸悲哀,仿佛此时需要帮扶的,是她而不是别人。 “你这个状态――”我的两个农业园都是作为产业扶贫项目引进蓥山县的,多少有些见识,知道“扶贫”这个词对公职人员和国企干部意味着什么,真担心她的情绪再次失控。 “没事,死不了!”她揩净了脸上的泪水。 日记从我与袁贵川离婚那天记起。 那天,从政务中心出来,望着袁贵川钻进那个女人停在路边的小车绝尘而去,我不堪的情绪瞬间崩溃,天塌下来的绝望感攫住了我的心,揪痛、窒息,至今不堪回首。 袁贵川出轨于一个离异女人。为了那个女人,他宁肯净身出户,妻女、财产均可抛弃,决绝如赴死囚徒。 我的妥协、退让、哀求,都被他无视。 他的理由很简单:她让他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 好像这些年来,我没能让他做成男人,而是威逼他做了女人。 见到万道的那一刻,就如即将溺毙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的霸道和痞气没有让我反感,反而给了我安全感。我忘了他曾经的欺负,也忘了他的浪荡德性。 他好歹是我的家乡人,是同学。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个哭诉的闺蜜都没有! 是的,孤傲清高如我,平日里连个能够交心的闺蜜都没有。 我不由坐下来,继续读下去。 二 行走在花椒林下,我的注意力不在结实累累的花椒上,虽然这象征着金钱和地位。 我的注意力在洛月身上。儿时的遗憾,燃烧成一种重口味的椒麻味道。 我曾经那么深刻地喜欢过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洛月。那时我读四年级! “喂,万道吗?在哪儿?”十一点半,洛月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说在农庄,并问她什么事。我希望她有事,却又害怕她有什么事。 “下午有空没有?我想请你开车送我去个地方。”洛月话说得很谨慎,态度犹疑。 “再没空都有空。去哪里?”我笑着问。 “没空就算了。”洛月显然不想勉强我。 我急了:“说,去哪里?” 她迟疑了一会儿,问:“真有空吗?” 我笑答:“我天生就一闲人!” “那就送我和同事去溪口镇天泉村。我们公司负责结对帮扶那个村七户精准扶贫户。中层一人一户,公司同事只有一辆车,我和另外一个同事――”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问。 “三点,公司楼下,一起出发,你看如何?” “我没意见。”我说,“你现在情况怎样?我的意思是――” “我没事。”她淡淡地说,仿佛正在吃泡面,平静地喝着老坛酸菜汤似的。 没事才怪! 在人生的最低谷,在哭诉悲情却四顾无人的时候,在坠落万丈深渊渴望得到别人拯救的时候,在刚刚撕心裂肺地哭过的时候,组织却要我去扮演救世主,去帮穷扶弱!不准质疑,不准抱怨,不准有任何畏难情绪…… 请问我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拿什么去拯救别人? 没事才怪! 但天性要强好面子的我,偷偷擦干眼泪,在同事们叫不到车的时候,强作无事,强作爽快地拨通了万道的电话。 天知道有多少眼泪被我咽下了肚! 怎么能没事? 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徘徊。 我没想到时过境迁,读到这段记录时依旧难以平静。 这则日记很长。 我想起那天确实发生了很多事。 好在万道还算有点文才,字也写得不错,写的又是我的伤痛,因此还看得下去。 我接着往下读。 我居然这么迫切地想重温一遍当时的悲苦,奇怪! 天泉村距离县城大约十五公里,浅丘地貌。 人在车上,只见一座座荒芜的小山丘,滚动的绒球似的往车后去,“球”与“球”之间,偶尔可见几块巴掌大的梯田,胡乱扔着几捆稻草。山丘之间,庄稼一样种着几座小平房,或者几间小瓦屋,弄出一些鸡鸣犬吠的声音,烟火气十足。几头水牛立在荒草疯长的山丘上,呆看着我们飞驰而过,忘记了咀嚼。 小车刚进天泉村委小院,便有几人上前热情相迎。 领头的是一个和洛月年龄相仿的美女,一副国家干部的样子,举止优雅得体,成熟稳重。听介绍,美女是天泉村第一书记,市国土局的副局长。 美女身后跟着两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文质彬彬的,一个是村书记,一个是村主任,大约都是大学生村官。 邹总带着一帮帮扶责任人去活动室听情况介绍。我是局外人,没事可做,便在小院里闲逛。 小院大约是原村小学改建的,隐约可见教室的影子。建筑物虽然陈旧,却收拾得很干净,绿化也颇用心。几株紫薇,几丛美人蕉,还有金鸡菊和蜀葵。宣传橱窗擦得一尘不染,内容既有村务公开那种套话,以及走到哪个村都能见到的所谓发展规划;也有实际的,比如建档立卡贫困户情况公示,国家的扶贫政策公示等。 半小时后,财险公司一帮人走出了活动室,表情凝重。 上车。说是去扶贫对象家了解详细情况。 村书记上我的车,坐副驾位置带路。一聊,果然是大学生村官,姓张。 张书记指路,把财险公司的七个干部分秧插秧似的分别送到对口帮扶对象家,便借口有事,双手一抱拳,先回村委去了。 我陪洛月去一个叫张天全的贫困户家。 车还没到地头,便闻到一股鸡鸭粪便臭,酸爽浓烈。我想洛月也一定闻到了,后视镜里,一对眉头皱得紧紧的,手掌捂在了口鼻上。 把车扔在村道边一块空地上,张书记指着一座低矮的小石头房子说:“那就是张天全家。他家没狗,我就不送你们过去了。” 我抽了抽鼻子,笑对依旧用手掌捂着口鼻的洛月说:“凭我的经验,这臭味一定是从那家人传过来的,你胃浅,还是别去了。” 洛月苦笑说:“我不去?任务谁完成?还用得着你的经验,这附近又没有别的人家。”说着,便朝小石头房子走去。 是一段石板路,不足五十米。路两旁是半人高的荒草,让人觉得肉疼的撂荒地。 臭味越来越浓,浓到人几乎无法呼吸。 我抽了一张湿巾纸给洛月,洛月像见到宝似的,赶紧展开,贪婪地吸着纸巾上的香气。 房子看上去至少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的了,条石砌成,小青瓦。陈旧、破败。 大门黑洞洞的,仿佛进不去一丝光线。唯一的窗洞连窗框都没有,只拿一只破米筛堵着,米筛上挂着几绺稻草,几片玉米皮。 房前是一块没有硬化的地坝。仿佛有千百只鸡鸭成天在此活动,地坝被踩得稀烂,遍地粪便,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走在前面的洛月站在地坝边,提着脚半天没敢落下去。我抢到她前边,替她踩出一条路,她才敢放下脚来。 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显然有老慢支,喘气跟拉风箱似的,“吼儿——吼儿——”还带着痰鸣,听得我都感觉胸闷。 主人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历,态度谦和,招呼我们在屋檐下坐。 屋檐下倒是干爽,却一样遍地粪便。 许是不满我们打扰,一只墙角土坑里刚泡过沙土澡的母鸡在我们面前死劲地抖着羽翅,并顺便拉了一泡热乎的便便,稀得能照出人影。 洛月喉咙明显动了一下,想吐。她表情难过地示意我礼貌点,接过主人递过来的凳子。我不忍拂逆,却见一坨干鸡粪粘在板凳端头,便收了手。那一坨干鸡粪一定来自一只高傲的公鸡,它一定曾昂首立于板凳端头,翅膀扑扇,打着鸣,留下了一坨肠胃正常的证明。 主人见我嫌弃,略显不耐烦,拿手一拂,便将鸡粪除去了。我担心洛月不肯落座,接过凳子,抽出湿巾纸一阵猛擦。 洛月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娇气,很随和地坐了,去和主人交谈。家里有多少人啦,主要有哪些收入啦,存在哪些困难啦,对国家的扶贫政策了解多少啦,详细地问,并一一记录。 我倍感无聊,转到屋后去看风景。屋后一座小山,小山下一片林地,林地里杂草丛生。 如果将林地围起来,养千儿八百只鸡鸭完全没问题。我想。我甚至都想好了该在什么地方砌鸡圈,什么地方摆食槽,还习惯性地论证了建造成本,养殖规模、效益等。 等我转回屋檐下,洛月已和主人交谈得差不多了,她提议去屋里看看。 这是个糟糕的提议。 在主人的带领下,我和洛月迈进了堂屋门槛。 堂屋宽约四米,深至少得有八米,倒是不窄。但因门洞不大,屋檐低,又没有窗户,采光不太好。 门口光线还行,能看出左右各有一个门洞。 右边门洞内,破米筛能透进一些光来,是厢房,像姑娘的卧室,墙上挂着几件女孩穿的衣服。 左边门洞内一团漆黑,不时涌出阵阵混合了人畜粪便味儿的恶臭。我疑心是猪圈,是茅坑。 靠左门洞墙边摆了一张饭桌,三条长凳。桌凳早已失去木头的色泽和纹理,黑漆漆的仿佛几十年没洗。这都罢了,让人无法直视的是几只母鸡正在桌上啄食一碗剩饭! 主人赶鸡时恶声恶气的,也不知是不满我和洛月来扰,还是痛恨鸡们在有人来访时不给他争面子,吓得鸡们在堂屋里一阵乱窜。那碗剩饭被一只鸡飞下桌时踩翻,米饭倾倒,覆盖在了一滩鸡粪上。 洛月一再拿湿巾纸捂住口鼻,有干呕的迹象。我不比她轻松,胃里一再翻腾。 饭桌下扔着一个食槽,里面汤汤水水的,弄得地面跟外面的地坝一样,恶心至极。 靠里墙摆了一张凉板床,上面扔着一床油光晃晃的棉被。刚从饭桌上下来的几只扁毛畜生,此时正站在棉被上,呆愣地望着我们。 右边还有一个门洞,是又一间厢房。洛月似乎受不了堂屋里的一切,提议去厢房看看。 “这间是一一住的。”主人带我们走进破米筛塞住窗洞的房间介绍。 正对窗户是一张木床,挂了一副蚊帐,帐帘下垂,遮住了床上堆放的衣物。我眼贱,居然发现蚊帐眼里积满了黑色的灰尘。 屋里没有别的家具,只在窗前摆了一张书桌,桌上摆着书本和墨水瓶。洛月看着那张书桌呆了许久。所谓书桌,不过是用慈竹搭架,搁了一块石板在上面的平台而已。 进屋以来,就对不讲卫生的这家人不以为然的我,心里居然有些颤抖。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穷成这样! 另一间厢房没有窗,里面漆黑一团。黑暗里,却见两只发亮的东西,阴森森的十分恐怖。 “床上是我妈,得过脑溢血,身体不好,起床坐一会儿就累,一天大多数时间都睡在床上。” 原来那两只发亮的东西,是张大妈睁着的双眼。 洛月去和老人家打招呼,嘘寒问暖,语气亲切。亏她个人刚经历离婚的打击,此时竟浑然忘却了自身似的,反倒同情起别人来了。 我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终于发现,这间屋子不大,陈设简单。除了主人得过脑溢血的母亲躺的这张床,就只有摆在床头的一个尿桶。我再次眼贱,不仅发现洛月正面对着尿桶,那桶里还不只装有尿…… 洛月要把每一间屋走遍,径直走向堂屋左边的门洞。主人却拦住了她,说那里头是厨房,又脏又乱,不用看了。我也以目示意,劝她别进,光闻味儿就晓得里面什么光景,小心进去吐个半死。洛月不理,非要进,并说不看完所有的房间交不了差,邹总饶不了她。 只好陪她进去。 进去之前先得适应两点:光线和臭味。光线太暗,主人舍不得开灯;臭味太烈,胃里翻涌。 厨房倒不算太窄。一口柴灶,一个猪圈。灶口正对猪圈,两头青猪把头搁在石头围栏上,眼睛盯着锅里的猪食。 洛月似乎想体验坐在灶前喂柴烧火的生活,但刚坐下便跳起身来,疯了一般冲出门洞去了。 我呆了,低头看时,原来凳子左边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是这家人蹲大号的去处!早上囤积的宿便,还留在口子上,没下去粪坑里…… 洛月蹲在地坝边沿呕吐,却又似乎胃里空乏,吐无所吐。我给她递纸巾,叫她擦擦,她擦着擦着,便眼泪直滚,明显哭了,不过只是瘪着嘴,没有出声而已。 我再次感到心在疼痛,而且痛感强烈。静立一旁,小心地陪在她身边,我不知道该说点啥。 突然发现,自从来到这家人的地坝,我就再没说过一句话。大约这家人的贫穷和苟且,实在让人无语。 原本只是简单的呕吐,不想吐着吐着竟然哭了。真是丢人! 万道被张天全家的贫穷与苟且惊到无语,我又何尝不是。但我心里不只有震惊,还有悲苦。在自己深陷悲情之时,组织上让我来帮扶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家庭! 这样的家庭,请问我怎么来帮扶?我能拿出来的,还能有什么? 热情?我自己都已心灰意冷,对亲人都提不起精神,又哪来的热情投入到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家庭? 同情和悲悯?那会儿的我,除了死,几乎自暴自弃到什么堕落就想干什么的地步,哪来的同情和悲悯? 自己的灵魂都需要拯救的人,却要扮演救世主去拯救别人! 我哭得有理! 我回到座位上,接着往下翻。 三 财险公司一行人结束入户走访,先不急着回城,却到村委活动室,汇总情况,听取村委的建议,舞弄了半天。 我为了照顾洛月业绩,几年来一直是财险公司不大不小的客户,和邹总熟。返城时,邹总一再表示今天我为他们公司的扶贫工作耽搁了半天,一定得吃个饭。但我另有所图,婉拒了。 我先把洛月的同事送到地头,然后对洛月说:“想请你吃晚饭,肯不肯给我个机会?” 我以为她不会轻易点头,毕竟脸色沉郁,似乎还浸泡在离婚的苦水里,不料她竟一口答应了:“就算你不请,我一个人也要出去海吃一顿,大醉一场。你请是最好不过。” 我们去她家附近的家常菜馆。 她点了四个菜:肝腰合炒、回锅肉、黄豆烧猪蹄、粉蒸肥肠。 “不减肥了啊?”我笑问,顺手勾了四个素菜。 “给谁减?减给谁看?”洛月颇有些愤世嫉俗之态,“从今以后,我要天天吃馆子,把自己吃成猪,吃成大象!去他妈的减肥!” “喝什么饮料?酸奶可以不?”我赶紧转移话题,不希望引起她激烈的情绪反应。 “切!”我不顺着她的情绪走,她显然不满意,朝我一挥手,一副堕落的样子,“跟你一样,啤的,要不干脆就白的。” “你不是从不喝酒吗?” “那是以前。” 一阵沉默。 在等菜上桌之际,我无话找话:“今天那家人,帮扶起来难度有点大哟。打算怎么帮?他家应该有个小女儿吧?” “邹总说了,明天再开个会,研究具体的帮扶措施。张天全确实有个女儿,叫张一一,养女,正读七年级。” 洛月的注意力被我成功转移,我心情轻松多了:“张天全没有生育?” “一辈子光棍,和猪生育?” “难怪!” “难怪什么?难怪要养猪吗?”洛月问。 “哈哈!”我竟被她逗笑了,“我的意思是,没看见他老婆。” “没老婆多好,像你小子一样,自由自在,换女朋友就跟换衣服一样随便。你们这些男人,哼!”洛月“哼”时,热气腾腾的粉蒸肥肠正好端上桌,她也不客气,举筷便夹了一截,狠狠地塞进嘴里,吃相像极饿了几天的乞丐。 “我天生就是浪子,好男人还是很多的。”我笑着说。 当初事业无成,遭前妻嫌弃,离婚时连孩子的抚养权都没拿到。我一度自暴自弃,玩世不恭。仗着后来发了点小财,手中有几个臭钱,我确实换了好几个女人,从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到三十五六岁的少妇,走马灯似的来去。其实我也很想找个实在点的女人成个家,好让下半辈子有个着落,可她们要么幼稚得可笑,要么势利得可怕,有的甚至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就要接管我的农庄,直接把我当傻子。 “你不是浪子,你是流氓!”洛月自顾自倒酒,一边喝一边说酒话。 “流氓就流氓!”我笑着说,朝她举杯,“为流氓干杯!” 没心没肺地闲扯。 她很快便醉了,烂泥一般。她执意灌醉自己,我想拦都拦不住。 醉了的洛月又哭又闹,揪住我撒泼,好像我是她家袁贵川似的,出轨在先,欺负她在后。 从菜馆出来,洛月的撒泼引来无数行人围观。路人都挺有正义感似的,纷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我行为不端,不是好男人,搞得我十分狼狈。 我只好强拽她回家。 她家我去过。那会儿我刚到蓥山县,一联系上她,她便迫不及待地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因为袁贵川做得一手好菜。说是请我吃饭,其实多半是想向我这个婚姻失败者证明她过得有多幸福。 我把她扔在床上,伺候她翻江倒海地吐。她在大街上已折腾了不少时间,到家后倒消停得快,吐了一阵便睡了。 我不打算回去。 倒不是因为猥琐,想趁人之危,而是心疼这个女人,担心离开后她出什么状况。 这些年见过的女人太多,没有一个让我心痛过。我以为自己早已练就铁石心肠,不想今天却两次体验到了心脏的痛感。我喜欢这种感觉。 在她家客厅沙发上歪躺下,久久不能入睡。我郑重地决定:追她,认真的那种! 从今往后,我就是追“月”人了。 洛月半夜起床,口渴要喝水。幸好我早给她备着。 她见了我,像见了鬼似的,吓得差点报警。我解释半天,她才松口气,却又审问:“你对我做了些什么,老实交代!” 我笑着说:“你吐得死去活来,我能对你做什么?只能端个盆子帮你接住呕吐物。不信自己回卧室看去。” 她果真回卧室去看,然后出来接着审问:“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留在我家干什么?” “我说不放心你,你信么?”我坏坏地笑。她看上去应该清醒了,我也该回去了,于是起身。 “我信你个鬼!你小子从小就坏,会有这么好心?”洛月还真不信,抬臂闻着衣袖,仿佛想闻出我的罪状来。 “不管你信不信,你应该都没事了,我也该走了。”我说着,就要离开。 洛月没有拦阻,也没有同意,只是不停地闻她的衣袖和衣襟。那上面只有浓浓的酒气,没有男人的气息。 我开了门,回头问:“老袁是净身出户?丫丫呢?”丫丫今年八岁,比我儿子小两岁。 “滚!”洛月恨极似的,“说了别在我面前提他,我恶心!” “好,我滚!”我笑着,出门并顺手关闭了防盗门。 夜已深,大街上静得出奇。高楼静立,霓虹闪烁。拖着长长的身影,我独自一人慢行,并不急着回家。我也没有家,那套租来的房子仅仅是个容身之所,连个女人都没有,算得哪门子家? 是洛月发来的:“你小子到手的便宜不占,以后可没得机会了!”后面是一串呲牙表情。 我也发了一串呲牙表情和两个字:“晚安!”我居然一本正经! 突然间很不喜欢与她的这种关系,太像哥们。 给他发那条颇为暧昧的 一向孤傲清高的灵魂仿佛突然间死去。 活着的那具躯壳急速地放纵,堕落,心甘情愿走向黑暗深渊。 从醉酒醒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受他的侵犯,却忘记了把自己狠狠地灌醉的初衷。 当发现自己好端端的时,又不由失落,仿佛未曾被一个浪荡子侵犯,人生就很失败一样。 等万道说要离开,心里一万个不甘,却又没出声挽留。 待他走远,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中,却又发去那条暧昧的信息。 我想成魔,从此自暴自弃。 然而一向放浪形骸的万道却一夜成佛,既没乘人之危,也没有顺着我的暧昧返回! 那一夜,我改变了对万道的看法。并在悬崖处勒马,收住了堕落之势。 荒唐如万道那种人,也能坚守自己的底线。 清高如我,怎么能自甘堕落! 年4月x日 我决定有计划地“追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制定一份追月计划以确保追月成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制定一套帮扶计划对洛月的帮扶工作很重要一样。同时,记录追月过程同样重要,有助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追月策略。一句话,我不想做那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情。 而制定追月计划,记录追月过程这种事情,对我这种搞企业的情场老手,二逼文青来说,实在易如反掌。 追月计划的第一步,是给她买一份早餐。 我借口去她小区外取车,给她点了一份早餐:稀粥、小笼包和卤鸡蛋。稀松平常,但自认为贴心。估计她宿醉之后会口渴,稀粥最合适。 她回得很快:正下楼呢,你在哪儿? 我回:小区门口,左边第三个门市。稀饭、小笼包和卤鸡蛋,喜欢不? 她回:还行! 看着她吃饭,狼吞虎咽的,一点不像原来那个洛月。失败的婚姻似乎彻底改变了那个温柔、纤弱,经不得一丝风吹的洛月。 “我吃饭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她几口刨完,擦着嘴问。 “不,挺好看的。我送你去公司吧。”我说。 “你成天没事可做?”她嘲讽地问。 “小老板都这样,无聊得很。”我一边给她开后排车门,一边保证,“但凡你需要,随时听候差遣。比如下次去天泉村。” “你觉得我该怎么帮扶那家人?”洛月却不去后排,排开我,径直上了副驾,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 “你打算帮到什么程度?”我问回去,并发动了汽车。 “不遗余力那种吧,我们邹总决心比国家领导人都大。” “你个人呢?” “公司都这样了,我个人还有啥可说的?就当转移注意力了。” “我觉得吧,先得帮他家把卫生搞好,太脏太臭,就你那胃,还不得去一次吐一次。”我眼前浮现出她蹲在张天全地坝边呕吐的样子,心里一阵紧。 “然后呢?” “然后帮他改厨改厕,修鸡圈,圈一个养鸡的场子,不然今天扫,明天拉,永远都改变不了。” “再然后呢?” “粉墙壁,添家具,买床上用品――” “还有呢?” “还有就是第一书记的事了。”我笑着说,“走产业脱贫是条不错的路子。我的九叶青农庄,带动了几十户贫困户就业增收。” “我把你的想法给我们邹总说说,谢了哈!”说话间,车便到了财险公司楼下。洛月下车,朝我挥手。 “丫丫呢?归你们哪个养?”我突然没来由地问。 她怔了怔,咬着唇,半天才说:“在我妈那儿。” 洛月是个连饭菜都不会做,极度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女人,如果丫丫由她抚养,她日后的生活估计得一团糟。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煮夫袁贵川确实是个不错的暖男,这也是他出轨的重要资本。 那晚万道装正人君子,我想要堕落都未能如愿。既然这样,那就好好地活下去吧。 不能做饭又怎样?极度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又怎样?女人这种动物,离婚则刚。我就不相信,离了袁贵川会死! 我不仅自己要好好地活下去,我还要帮张天全一家活得有个人样儿! 那一晚,从万道离开,我就再没能入睡,胡思乱想了大半夜。 思前,我把自己的婚姻生活,个人在家庭中的各种不是都审视了一遍。 想后,我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好好地梳理了一遍。 我决定尽快从离婚的悲情中走出来,尽管会很难。 走出来,需要内在动力,也需要外部契机。 扶贫,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转移注意力的契机。 那就好好扶贫吧,也许它比工作更能让人纯净。 追月第二步:关心她的关心。 洛月眼下最关心的事情,理论上有二:一是尽快适应没有袁贵川的生活,二是帮扶张天全一家脱贫。没有袁贵川,洛月还有早就在两年前就搬到蓥城居住的父母可以暂时依靠,在她来说,适应新生活可以慢慢来,不用太着急。剩下的就只有帮扶任务了。我得紧紧抓住这一点,大献殷勤。 午饭时间,我给她发了条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ry/7568.html
- 上一篇文章: 十拿九稳ldquo搞定rdquo
- 下一篇文章: 黔中文学王杰会唱山歌的网友总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