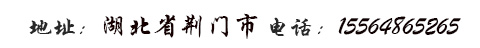群山丨方雁离小说野马桑一
|
方雁离,云南师宗人,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于《山花》《钟山》《作家》《星星》等,获“年度云南省优秀作家”奖。 “因为我也和你一样。和你一样孤独,和你一样不能爱生活,不能爱人,不能爱自己。”忘川里 急速的衰老在她的体内蔓延,在永恒不变的少女面容之下,她的心在突然之间萎缩,干瘪,布满了皱纹。她甚至看到它的颜色正由红变褐,由褐变枯的渐进。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她再一次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四周静寂黢黑的群山,像伏在远处等待某种命令的黑魔,眨着嗜血的眼睛,红的、蓝的,绿的,在她看不清的地带汹涌,仿佛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它们就会黑压压齐刷刷地向你挤轧过来。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在之前无法计算无从回顾的漫长光阴里,她的亲人们几乎都从这里走过去了,叔叔、婶婶、堂弟,村子里许多沾亲带故的人,他们都从容不迫地从这里走了过去。叔叔不认识她,婶婶不认识她,从这里走过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再记得她,而她却记着所有的人。这些记忆就像烈火在她的体内熊熊燃烧,像大江在她的体内怒吼奔腾,这样从不止息的燃烧和奔腾推涌着她体内冰冷的死血像海水涨潮一般一波接着一波地汹涌。就在刚才,她的母亲也从桥上走过去了。这让她觉得那股一直积攒在她体内的力量在瞬间陷落,从天灵盖开始,它们顺着脚掌心,沿着大地的脉络钻入地心深处,她感到了自己的坍塌、虚脱、无妄。是的,坍塌、虚脱和无妄,就像一棵急速枯朽的大树,养分顺着庞大而盘根错节的根须迅速流失,上面枝桠节节败退,下面大地层层充盈。她看到湖堤上有一株水晶兰慢慢钻出地面,她那奔腾不息的力量随着水晶兰的拔节一层又一层由内而外,抽丝剥茧般地被抽离。在水晶兰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枝干上,一朵花苞随着她的被抽离渐次打开花瓣,再逐一微拢成半开半合状,有若水晶状的菸斗微微下垂,在忘川里散发出幽幽的白光。平日沸腾的忘川湖此刻静得像死了一样,除了听得到水晶兰的拔节盛开,再听不到一点儿别的声响。她的眼睛里,看到的全是声音的形状,那些围着奈何桥的扑腾,声嘶力竭,撕心裂肺,到处都是她完全能够看清楚的声音的形状。她觉得相比于怨恨和牵念,永不被人记起才是更有力的杀手,它竟然把她吮吸得一干二净,让她在突然之间瘫软、枯竭。松开原本紧张有力的四肢,她骨架庸散,仰面朝天,在别人的扑腾之下随波起伏,群山在脑后越来越近,面前的奈何桥越来越远。忘川水顺着山的脊骨从上方飘落下来,她感觉到了泪水的温热,像小时候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光着脚丫踩在土地里的温热。她想她祖祖辈辈的泪水也许都从这里飘落下来了,于是她突然想到那些埋在黄土之下、棺材里的祖祖辈辈的肉身,他们腐化成一滩又一滩泡着骨头的水渗透棺木,通过泥土的层层过滤流进了忘川里?应该是这样的,唯有如此,他们身体里蓄积一生的泪水,才算是真正流干了吧。她又想起了那个孩子,担在野马桑树的枝桠上,他破败残缺的身躯,长出了木耳、树花、白苼,他的小小的陷落的眼窝里,噙着乌黑的野马桑……一切并不因为她身在这远离尘世的忘川里而改变,相反,她一直看见他在那个枝桠上,斧头砍过的小小身躯的断裂,还沾着腐皮烂肉的头骨和脑髓被村子里的人拿走了,他们将它放在火塘边烘烤,研磨成粉,作为一味人间奇药吃进了精神病人的肚子。她常常想他也许又活了,像她活在忘川里一样的活着,也许他活在了那个吃下他脑髓的精神病患者的身体里,他在那个身体里嘲笑他荒谬绝伦的死亡,哭泣他一无所知的懵懂的人世,或者,他也在忘川里,紧紧追随着她,试图再回到她的身体里来。她已经漂到了忘川湖的最边缘。那些倒映在忘川湖里,照得忘川里一年四季清冽通明的星光的植物,竟是那么具体地呈现在她的眼前。在头顶,遥不可及的上方,巨大的蓝紫色的奢香魔芋正贪婪地餮食着湖里的灵魂,遍野火红的长着细细长长针形花瓣的彼岸花,每一个长长的针尖上都挑坠着亮闪闪血色的红艳,还有吐着蛇信子的瓶子草,那星光则血淋淋垂涎欲滴地坠在信子前端,白色的娃娃眼,一朵黑色的星嵌在一团肉一样的青白色里,与人或动物被取出的眼球一模一样……在这无时无空的忘川里,她第一次感觉到空间概念的存在,之前四野茫茫的星空和身子下面的湖泊,以一个一个具体的形态呈现在她面前,仿佛是一直等待她到来的样子,却又是她根本不想要的极力排斥的未知,也是她在内心深处期待了许久许久的想要获知的世界。死水里静静漂着死去的苍白的魂灵,发霉的白色躯体上正在长出奇形怪状的依旧挑着星光的植物,她想那孩子也许就在这些死去的静静漂着的白色发霉的躯体中间,他的身上,应该也长出了一株有着黑色瞳孔的娃娃眼。她看到散发着奇香的佛手,五个红色的畸形的手指上闪着宝蓝色的星光,正扭曲而变态地向她伸过来,她感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不,我不能死,我不能如此放任死亡,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忘川里的瀑布像断了线的珠子,丝丝缕缕纹理清晰,它由人的泪水流淌而成,互不交汇,缓缓飘落,任它如何细密都可以分出哪一条线哪一条河是归属于哪一个人。从她来到忘川里,孟婆就一直坐在奈何桥头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一是把忘川里悬挂的泪瀑和着忘川水酿造出孟婆汤;二是兜售她的孟婆汤。就像学校门口卖木瓜水的老妇人,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在那里的,她在那里多少年了,也不知道她的木瓜水为何总是供不应求,没有人会对这种问题产生兴趣。但是她常常会去想,这个孟婆是不是她的祖祖辈辈经过的那个孟婆,如果是,那么她见证过自己的几生几世?如果不是,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为什么可以在忘川里做着独一无二的红火买卖?不过,她想归想,却始终没有去问,她觉得问了孟婆也没法回答她,或者她和卖木瓜水的老妇人一样忙到顾不上跟她讲一句多余的话,她只知道收钱找钱,问你要原味的还是加了玫瑰糖的,她甚至顾不上伸手给你将碗递过来,她只负责不停地往碗里面加水,人们自会抢着自给自足。而孟婆汤和木瓜水一样,也只分为两个品种,琥珀色微苦的一碗叫结魂汤,清冽甘甜的一碗叫忘情水。喝下结魂汤的人留在忘川里,不仅不会忘记今生,还能再次记起隔世往事,想要走过奈何桥,入得鬼门关,进入轮回得等九生九世。而喝下忘情水的人则可以将今生的爱恨痴怨忘记得一干二净,走上奈何桥通向轮回。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像她这样什么都不喝的,既不需要记起隔世,也不需要忘记今生,但如果想进入轮回就得在忘川里等上三生三世。每当旋起的水龙环绕上她的身体,她总是感到烧灼的剧痛,这样的时候,她就知道孟婆正在为与她体内那股力量有关的人酿制药汤。每一次她都认为自己会被这样的烧灼疼死。尤其母亲来的时候,疼痛更为剧烈。一向懦弱的母亲在喝孟婆汤这件事情上却是她从未想到的果敢决绝。孟婆用她那双与奶奶的手一样又冷又瘦的手拉着母亲,对母亲说着她一边盛汤一边永生永世都在重复的那几句话。当她说到,可怜的孩子,喝下这碗忘情水,你就可以忘记你爱过的人,经过的事,恨着的人,受过的苦,你一身的悲与怨就彻底解脱了。母亲便以一心赴死的壮烈毫不犹豫地抬起那碗忘情水一咕噜倒进肚子里,她面容平静地走上了奈何桥,眼中没有任何哪怕一丝丝的波澜和留恋,甚至没有回顾一眼奇花异草、洒满星光的忘川里。她看到走在奈何桥上的母亲有她从未见过的美丽,她想她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这种美丽了,她的母亲,脸上盛开着彼岸花,从黑幽幽的头发到轻快从容的步履都披满了星辰的光辉。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憎恨母亲的。也许因为母亲的心无旁骛,那种表现得像个又聋又瞎的人一样的心无旁骛,令人绝望的寂静的心无旁骛,带着仿佛是在石柱子上雕刻出来的无懈可击的从容,没有人轻易可以打破的从容;抑或是在她有生之年就早已开始,只是之前一直未曾察觉的对母亲软弱无知的愤懑、怨怼和憎恨。是的,应该是这样的,后来她在这无时无空的境地千百次想起,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从那碗忘情水开始,她对母亲的怨怼、牵挂转向了明确的憎恨,仿佛一生的所有悲苦无奈都在那时那刻涌上心头,空空荡荡如丧钟之音在她的胸腔里回旋、撞击,她再一次觉到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但是她又不停地提醒自己,我的躯体是深埋在土里了,但是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的魂灵还活着,只要我还在忘川里,在死不能死,生不能生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忘川里,我体内积攒的力量就不能消失,它们早就与我的灵魂合二为一了,怨怼,愤懑,仇恨,恐惧,以及微不足道的牵念,它们怎么可以消失呢?她想它们跟她的灵魂一起,长在了那棵洁白透明的水晶兰里。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竟然扒开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积攒着力量的人群,一直扑腾追随到桥的尽头。但是她的嘶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又想如果她死了,那还是死于被遗忘,这种被所有人遗忘的虚脱感像一只拳头砸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使得她一直坚持一直积攒的东西变得毫无意义。她觉得真正的孤独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占领她的,从那时候起,她常常感得虚脱、精疲力竭,以至于她又常常害怕她会死于这样的痛苦、绝望和了无生趣。她总是听到人们说,在忘川里之外鬼门关之内,有着一个与人间相同的世界,喝了忘情水的人到那里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同样面对出生、疾病、衰老、哀苦和死亡,那里有集市、街道,乡村,土地,他们在那里继续面对社会不同的分工劳作。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她总是想那里也应该有学校卖各种小吃的妇人。她也想到那里会有奶奶,村子的麦地旁边有野马桑树,还有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近来,她感觉那个孩子长大了,好像长高了一点,走路也不再摇摇晃晃,他一直跟着她,她总是能听到他幽幽的呼吸,均匀的,慢慢的,一下一下像是熟睡着的呼吸,他跟在她身后,有时候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总是在她转身寻找的时候又消失不见。她还梦见过他,小小的嘴里面衔着碧绿的还带着稀泥的青苔,那些青苔缓缓蔓延到他的脖颈、胸腹、四肢,他看到他撵着她,蠕动着小嘴,她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她知道他在说下雨了,他冷,他想回到她温暖的子宫里去。她总是被这样的噩梦惊醒,醒来之后她又觉得他来了,附着在忘川湖里的每一个人身上,看着他们在湖水中浸泡着的身姿,有的人蜷着身子睡着了,她就感觉到那孩子蜷在她的子宫里,她甚至感觉到他在里面伸懒腰、蹦跶,她会想到太阳热烈的烘烤,他担在野马桑的枝桠上冒油、破皮,嫩嫩的冒出油的身体……除了恐惧还是恐惧。她想他早已在那个未知里等着她了,而奶奶,制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也还会在那里等着她或者找到她,她对她的生活无孔不入,她将继续陷入生无可恋,死无可依的状态。想到这些的时候,她对那个未曾见过的世界又是望而却步的,她甚至会出现一种前生空白的苍茫,以为所有经历过的都只是一场梦而已,前面等待她去进入的才是即将上演的梦中故事,这样她就分不清什么是脑袋里想出来的,什么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的。但是,她却不愿再想起母亲了。在人间 空气中飘忽着时浓时淡的烟火香,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烟火的燃烧是有香味的,虽然它有时候很呛人,但远远闻到总是令她觉得温暖而愉悦,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夹杂着金桂的香气,闻起来就更加舒服了。突然,她闻到了另外一股香甜滑腻的气息,像苹果,或者香蕉,火龙果和葡萄的气味也有一些,密密匝匝、自由自在地从不远处传过来,和四周正在燃烧的烟火气,暗夜刚刚绽放的桂花香混为一体。她便想起了奶奶,仇恨再一次升腾而起。她竭力想要镇静下来。在忘川里被抽空之后,她曾经莫名其妙地获得了一种类似于放下怨恨的短暂的轻松感,像是卸下一副压在身上成百上千年的千斤重担,她甚至有些舍不得切断那种轻松的感觉。然而,这种情绪对她的牵制,就像她身上的血一样,不仅混合继承了她所不了解的祖辈的基因,还有她拒绝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奶奶的、母亲的血液,它们与生俱来,不可逃避。从她在母亲肚子里发出的第一瓣小胚芽开始,它们就排山倒海地跟着来了,她最多可以短暂地忘却它,有那么一阵子一阵子地不去想起它,真正放下,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好闻又好吃的气息确实是奶奶的专属,她知道在村子里除了奶奶,没有人享有这种特权。是的,奶奶总是义正辞严理所当然地独占这种特权。她总是说,你别碰火龙果,吃了脸上会长雀斑,你别碰桂圆,吃了脑袋会越来越小,你别碰葡萄,你的脑袋会小到像它们一样装不下东西,变得越来越笨,甚至吃个鸡肠子都有各种不让她吃的理由。不过,奶奶没有为母亲找过哪怕一个理由,母亲还是不敢吃那些东西。她还记得她在山上吃了同样散发着香甜气息的野马桑,甘甜、乌红、细小的野马桑颗粒像一粒粒小灯笼,她咀嚼着小灯笼的时候想着自己嘴里嚼的是苹果、葡萄或别的什么东西,想着母亲一再交代她小灯笼上附着巫婆的魂,吃了会变呆变傻还会死人。她还是吃了,想着这些稀奇古怪的莫名其妙的道理吃,脑袋里放电影一般反反复复都是奶奶和母亲对她说这说那的画面。她想着她明明看到母亲在烈日下忙活的间歇也刷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小灯笼昂进嘴里,不同的是奶奶她吃下了很多的火龙果,桂圆和葡萄,脸上长出了老年斑,母亲吃下野马桑脸上长出的是大颗粒的汗珠子。不过,最荒唐的是她那时候不想长雀斑,不想脑袋里没有东西痴痴傻傻,她一心想做个美丽又聪明的孩子,想让母亲开心,特别是心存侥幸希望奶奶会喜欢上她,事实证明,这的确是她所有的想法之中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一个。然而,那孩子就以那样不可理解的方式死了。自从他被担在野马桑树的枝桠上,她再也不会想吃野马桑了,她总是感觉顺着食道翻向舌尖的味道,甘甜微涩里混合着孩子的皮肉,她觉得世间一切的野马桑树上都长着一个孩子的躯体,那些乌黑的小灯笼般的果实里都眨着孩子的眼睛,果实紫红色的浆子里淌着那孩子身体内的碳水化合物。那些野马桑的枝叶汲取了他的血肉,长得蓬勃诡异,她常常想起它们,野马桑和孩子,他小小的被斧头一破为二的身躯长在野马桑树的枝桠里,他长出了细长的枝枝丫丫的小手,茁壮的短短粗粗的小胳膊小腿。她的胃总是一再翻江倒海地提醒她,那孩子长在野马桑里,那孩子长在野马桑里,那孩子长在野马桑里,说不定在那孩子之前,就有许多与他一样的孩子长在野马桑里。她对他没有牵挂,从来没有,她只是因为他曾经在自己肚子里长了七个月而对他心怀愧疚,这些愧疚却愈发加剧了她每每想起就停不下来的害怕和恐惧。从开社的日子到中元节的来临,中间有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忘川里的许多人都可以游移到人间去。虽然每日里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往桥的方向扑腾,但比起平时,终究还是安静不少。他们有的去一会儿就返回来,有的去一两天返回来,有的却到中元节才不得不回来。她从来不想出去,尤其是母亲过世之后,她好像对这个唯一能给她带来点时间感的日子更加麻木不仁。五点多的时候,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十字路口,她看到母亲站在黄昏里烧纸,流窜的青烟飘到火烧云里。她想母亲也许还在那里。这样想的时候,奶奶的身形划过她的脑际:母亲已经不在了,家里再没有一个可以出来烧纸的人了,也许,奶奶会变得跟从前不一样,她也没有理由一直保持从前的样子了,再说,她现在还保持那个样子给谁看呢?她使劲摇摇头,不!怎么可能?奶奶一直像个大债主,世间所有人都欠她债的样子,她怎么会给别人烧纸呢?如果她真的来烧纸了,也许自己心一软就原谅她了,这不是我需要的,我不能原谅她,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这样的念头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但她又是多么希望奶奶做出一件在她看来是善良和温暖的事情啊,哪怕一件,只要一件,她也许就不用这么矛盾这么沉重了,她也许就可以给奶奶找出一个不得不原谅她一些的借口,她是多么希望啊,怀着这种明知不可能却放不下的侥幸,她还是从忘川里出发了。没想到,刚一出门就下起了暴雨。头顶上笼罩着厚重的铅灰色,天空被它压得很低很低,雷声像石板在头顶轰隆隆地翻滚,仿佛只要一抬手,就能将手伸进那些石板的缝隙里,实实在在地抓握住一把闪电,但她不敢这么做,她就像害怕管不住自己的手似的将手紧紧藏在两个胳肢窝里,几道闪电撕裂天际,她吓得紧闭眼睛,蜷作一团。忘川里长年累月的星光散射,她的眼睛已无法承受任何强光的刺激,哪怕一缕闪电,都会使她感到魂飞魄散的恐惧。雨水足有一米多深,水面飘满了烂菜叶、塑料袋、果皮残渣,它们和熏臭的淤泥一道灌向临街的店铺。继续往前走,雨渐渐变小,路上烧纸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三三两两的聚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撑着伞,有的躬着身子烧装满了冥币和衣物的纸包裹,有的已经烧完了在泼水饭,水饭随着挥出去的勺子在空中划出长长的抛物线,这总是让她想起天空抛洒的白色冥币,圆的、中空的白色,像雪片一样在天上飘洒。她又听到那孩子窸窸窣窣地来了,以往这个日子,他总是踩着金黄的落叶随风在地上滚出几个圈,再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她看得到他的样子,小小的破败的衣衫,脑门上方留着和别的孩子一样的桃子形的一撮黑头发。而今日,他跟着雨水漂来了,脏兮兮的脸蛋上挂着黑色的污泥,身上披着烂菜叶烂果皮,她想他一定是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的,好像在这样的日子,她所能想到的他的来路也只有下水道了,她看着他向她迈开小小的步子,张开一双污浊的小手,摇晃着过来找她了。她闭上眼睛,感觉到他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心口上,他的嘴角、小颧骨、小眉毛、小鼻子,到处挂着污泥,他在她的心口上踏着小碎步,污泥滴答滴答地一小块一小块落进她的身体。每当这样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必须镇静下来,即使心怀恐惧和怨恨,也要学着镇静下来,她想学会安静地思考,不激起一丝一毫波澜地去回忆。脸朝上,深深地吸气,再缓缓地吐出,就这样慢慢地,冷空气塞满了她五脏六腑的每一个角落,她把他从自己的身体里脑袋里一点一点地逼了出去。她的牙齿咯咯地打着寒战,被雨水湿透的身躯像冰裂般咔嚓哆嗦起来。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能够觉察到她的存在。老老少少都在静静地看着那个身材纤瘦的中年女人忙活。她神情肃穆虔诚,动作小心谨慎,细长的手从一个白塑料袋里抓出大把粉白的碳灰,在石台上划出一个大大的,直径约两米的圆,接着,又在左边画了一个与圆差不多大的“十”字。碳灰落地后变得潮湿,成了粉粉的肉红色的细小颗粒,像极了她身上的鸡皮疙瘩,于是她哆嗦得更厉害了,身上的鸡皮疙瘩似乎厚厚地堆积,又簌簌地坠落一地。她神思恍惚,是的,是她的母亲来了,面前的这个人,她重复着她的母亲每年这个日子都在重复做着的事情,她闻到空气中有微微的麦芒和烤烟味夹着田野的汗香,那是从呼吸和毛孔里发出的根深蒂固的气息,她熟悉这样的气息,母亲的气息。她仔细看她,粗大的双臂,微躬的后背,脸膛黑红,是的,她就是母亲,她长年累月在田野劳作的母亲。但是,她亲眼看着母亲从奈何桥上走过去的,她已经不记得她了。她突然觉得失落,一切都只是幻想和奢望而已。不过,她又迅速从中寻得了一种自我安慰,就算再没人记得她了,起码她在这个地方见到的这个人,给了她暂时的亲近感,也许在冥冥之中,母亲与她还是有着一种来源于血亲的感应也未可说。忽然,那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打破了沉默,奶奶,我们赶紧烧吧,一会儿老祖宗等急了发火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蹦到车边,抓了几个白色的大纸包裹抱在怀里,纸包裹太大,遮住了他的半张脸,鼻子以下都看不见。他的妈妈忙跟着给他遮伞。哎呦!我的小祖宗,地上湿淋淋的怎么烧呀,赶紧放回去,小心弄潮了燃不起火来!老太太生怕纸包裹落地沾水,慌忙火急火燎地接住。奶奶,您不要叫我小祖宗,小心老祖宗听见了不高兴,骂我们不懂事。小男孩仰着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看,又刮大风了,一定是老祖宗生气了。他们被小男孩逗得哈哈地笑了起来,像是正在办一件大喜事一样的眉开眼笑。她便想到她的奶奶也叫她祖宗,她叫她祖宗的时候声色俱厉、气急败坏,拐杖擂打着地面,带着一种诅咒的恶毒,她的心脏和神经就跟着拐杖的节奏抽筋打抖。她尤其记得奶奶那双握着拐杖的手,松弛的打着褶皱的皮堆在上面,总会让她想起村子里死去的、平躺着等待装进棺材的老人,他们穿着严丝合缝的新衣,脸上盖着猩红色的盖脸布,全身上下能看见与骨肉相关的东西,就只有一双交握在胸前、长满老年斑、青筋暴露、又冷又瘦的手,像一把堆满了褶皱的、僵硬的、阴森森的老骨头。但是这些都只是表象,只要奶奶裹着的小脚一动起来,她就是精神抖擞的,活像村子里那只竖着血色鸡冠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大公鸡的嘴就长在拐杖的前端,但凡被她撵到了,必得啄个头破血流的,她亲眼看见妈妈和婶婶曾多次被它啄破过脑门。那天,她亲眼看着他们将她的身子从塘子里捞上来,奶奶杵着长了公鸡嘴的拐杖,深陷的眼窝里射出猫头鹰一样阴森的光,公鸡嘴点在她没有体温的胀满了水的肚子上:死了!死了就死了!肚子里的种还活着!赶紧给她拿出来,不要让他们变成妖精出来祸害人。于是有人拿了刀子剖开她的腹部,将那孩子从子宫里抱出来,他蜷着肉红肉红的小身躯,攥着小拳头,那人拉着他的两只小脚将他拎起来,用手掌拍了两下他小小的巴掌大的背脊,他就哇地一声哭起来,开始的一声清脆响亮,继而绵软无力。竟然真的活着,那人说。奶奶的拐杖点在他小脑袋旁边,她真担心那一拐杖点下去他小小的拳头般大小的脑袋就会马上破碎。这妖孽!必须马上处理,按老规矩,断作两截,担在野马桑树上。她就这样亲眼看着奶奶发号施令剖开了自己的肚子,再发号施令把那孩子活活断开了。从那以后,她常常觉得自己的肚子上豁着个大口子,要么从里面钻着风,要么从里面灌着水,有些时候,世界空荡荡的,除了晃眼的地霭边沿阴冷的光什么也看不见,那孩子就来了,不见头不见手的,只是挪移着小小的苍白的屁股和小腿向她走来……(未完待续)往期回顾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七)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六)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五)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四)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三)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二) ◆群山丨吕翼长篇小说:比天空更远(一) 来源丨 昭通日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tx/8368.html
- 上一篇文章: 准谁家老婆是此生肖,前世修来的福气,注
- 下一篇文章: 答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