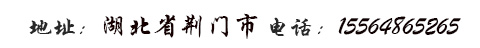长篇小说寒凝大地连载丨第二十八回无辜
|
儿童医院白癜风外用药 http://m.39.net/pf/a_4491885.html 第二十八回:无辜百姓遭涂炭,有为青年赶豺狼 残月如钩霜雪飞乱云翻滚风雨狂 无辜百姓遭涂炭有为青年赶豺狼 潮白河东唐洞村的刘文亮、王斌、胡芝三个小伙子,运气真不错,刚刚参加八路军,就赶上部队培训。在冀东独立团军校学习了三个月,毕业典礼时,都得到了韩团长和胡政委的表扬。 也是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几个小青年,从小苦出身,一家比一家穷。十来岁了,还光着屁股。喊他们“光蛋”不行,还须在前面加一个形容字:“穷”。 这三个穷光蛋,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儿,一起光着屁股长大。 唐洞村,洼地多。洼地积水,到处是水坑子。水坑子是乡下毛孩子们的乐园。 夏日炎炎似火烧,热得人们没处藏没处躲的,连趴在树杈上绿阴里的知了,都热得发昏似的嘶叫:“热——” 刘文亮、王斌、胡芝三个毛头小子,在村头老槐树下,扎在一起玩儿老虎吃小猪。 刘文亮说:“太热了,咱们不玩儿老虎吃小猪了。” 王斌说:“行!” 胡芝说:“文亮,听你的,你说咱们玩儿什么?” 刘文亮说:“游泳!” 王斌说:“哈,快别提游泳了。我和胡芝还行,你呀,属秤砣的,掉河里就沉底!” 刘文亮说:“你们会水,到深处玩儿,我不会在浅的地方练狗刨儿,还不行?” 胡芝说:“谁说不行了?” 王斌说:“行!” 三个毛孩子一蹦老高,争先恐后地往唐洞村南跑。 这一带水坑子多,浅的大,像碟子;深的小,像碗儿。 刘文亮说:“今儿就来咱们三个,人少,挑一个小水坑子,玩儿打水仗,怎么样?” 王斌说:“小水坑子深。” 胡芝说:“文亮别到水坑子中间去,再说,鸡蛋壳大个地方,咱们俩好歹会点儿水,能有什么危险?” 王斌说:“行!” 于是,三个毛孩子,噼里啪啦脱光衣服,跑进水坑子里,把原本平静的水面,激起一串串水花。 打水仗,得分拨。三个人咋分?咋分都不合理。于是,不分,打烂仗。其实,不分拨的打烂仗,更好玩儿。 三个小小毛孩子,把水坑子闹得劈里扑腾,水花四溅。 多么好玩儿的游戏也有感觉厌倦的时候。 三个小小毛孩子,累了,乏了,爬到水坑子岸边,在沙滩上折跟头,打把式,汗流浃背,满身满脸沾满了细沙,一个个土猴儿似的。他笑我,我笑你,笑翻了你我他。 笑够了,笑饱了,王斌说:“咱们下水里,把浑身的细沙洗洗,躺对岸的高粱地里凉快凉快。” 胡芝说:“好主意!” 于是,三个毛头小子,扑腾跳下河。 王斌说:“文亮,我和胡芝游到对岸去。你呢,不会水,从岸边儿绕过去。” 刘文亮说:“我才不从岸边儿绕呢,河岸上的芦锥草长得可凶了,扎屁股,我从浅水地方走过去。” 王斌说:“行!” 胡芝说:“王斌,咱们俩人紧挨着,让文亮在中间,扶着咱们俩的肩膀,一块儿游过去,好玩儿吧?” 刘文亮高兴得直蹦脚。 王斌说:“行!” 于是,胡芝、王斌先趴在水里,刘文亮插在他俩中间,向对面游去。 刘文亮叫嚷道:“真好玩儿,真好玩儿!” 不成想,胡芝和王斌吃力过大,渐渐分开了,愈来愈远,终于,刘文亮沉入水底。 胡芝和王斌游到对岸,坐在沙滩上,一个个急得嚎啕大哭。 王斌说:“我下去,下去救文亮。” 胡芝说:“我也下去!” 王斌说:“行!” 刚刚上岸的胡芝和王斌又跳进河,扎进水里。 王斌扎在水里摸啊找哇。 胡芝扎在水里找哇摸啊。 王斌把头探出水面,问:“摸着了吗?” 胡芝把头探出水面,问:“找着了吗?” 正在王斌和胡芝晕头转向的时候,就听水坑子的岸边大声地叫唤:“王斌,胡芝,我在这儿呢!” 王斌和胡芝听到喊声,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刘文亮已经爬上了岸。于是,他俩又往回游,一齐跑上岸边。 王斌叫道:“文亮!” 胡芝问:“你不会水,怎么游到岸上来了?” 刘文亮说:“我当时沉到河底,心里想,完了。可是,我并没有慌张,在水底下揪着水草,照直往前爬,爬着爬着,我憋得实在受不了啦,就站了起来,想不到,水面连我肚脐儿都没有没过去,哈,多逗呀!” 王斌说:“你可把我俩吓坏了!” 在朋友处于危险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去营救,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 自此,这三个毛头小子,愈来愈亲密,说生死之交,并不为过。 这仨人,一同参加八路军,一块儿进入冀东独立团军校接受培训。今儿个,又一起回村,高兴地说了一路,笑了一路。 他们走近黄土岭,再翻过横在前面的一道丘陵,故乡唐洞村就在眼前了。 刘文亮说:“二位哥哥,眼看就进村了,咱们还不进‘独龙岗’小饭馆撮一顿儿?我掏钱!” 胡芝说:“你属狗,我属鸡,我比你大一岁,大一岁也是你哥,怎么能叫你掏腰包呢?” 王斌说;“你这话说的,不是在将我的军吗?你属鸡,比文亮大一岁,我属猴,比你大一岁,怎么能叫你掏腰包呢?” 刘文亮和胡芝都笑起来。 王斌发了一会儿愣,说:“你们这俩坏小子,是不是商量好了,算计傻哥哥呀?哈哈……” 三个人一面说笑,一面朝“独龙岗”小饭馆走去。 在顺义潮白河东,唐洞这个村地形特殊,背靠大山,村前是一道丘陵,这道丘陵东西走向,东高西低,远远望去,仿佛一条龙。许是这个原因,聪明的唐洞先人,给这道丘陵取了个“独龙岗”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 小孩子们把水坑和独龙岗作为极好去处,他们玩耍的地方,非此即彼。 冀东流传着一句民间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老天爷真的很讲信用,正月十五这天真的下了一场大雪。 刘文亮、王斌、胡芝这三个毛头小子,每个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不约而同,来到独龙岗。 王斌和胡芝的灯笼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纸糊的。 唯有刘文亮的灯笼,与众不同。他的灯笼是用橘子皮做的,中间插上一小截红蜡烛,四条短线均匀地穿进橘子皮,拴在一根小棍儿上。 王斌说:“亮子,你这叫啥灯呀?一丁点儿都不亮!” 刘文亮说:“谁说的不亮?这不,也能照出丁点儿亮光嘛!有点儿亮光就能照路!我姨姐说,这叫小橘灯。城里的小孩子,都时兴玩儿这种灯。” 胡芝说:“城里的你姨姐来了,倍儿漂亮吧?” 王斌说:“你姨姐从城里来,一定给你带许多好东西吃,是不是?” 刘文亮说:“橘子,桂花糖,啥都有。”他一面说,一面掏口袋,说,“王斌,胡芝,你们俩,把眼睛闭上,把手张开。” 王斌和胡芝不知啥馅儿,一个个都把眼睛闭上,把手张开,伸给刘文亮。 刘文亮放在王斌和胡芝手里每人一块糖,然后说:“睁开眼吧!” 王斌和胡芝睁开眼睛,发现他们原本空空的手里多了一块糖,两个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三个小孩子提着灯笼在独龙岗上又追又跑。玩儿得正热闹,漆黑的天上,又悄悄飘起了雪花。 还是刘文亮的主意多,他说:“咱们把灯笼挂到树上去,玩儿吃雪花儿!” 王斌和胡芝齐声说:“行,看谁吃得多。可有一宗,谁都不许说瞎话!” 刘文亮说:“那是呀,谁要说瞎话,叫谁爬着走!” 于是,三个人玩儿起了“吃雪花”。 玩儿的兴致正浓,好像远远地传来了大人们的喊叫声。 三个毛头小子停下比赛,侧耳仔细听,仿佛是家里的大人们在呼唤他们回家。 刘文亮的耳朵尖,最先作出判断,说:“你听听,好像是王斌的妈妈,是的,是你妈妈在叫你!” 王斌细细地听听,点着头说:“许是我妈妈,是,是我妈妈在叫我!” 胡芝说:“要不,咱们回去吧,回家晚了,又该挨揍了!” 刘文亮说:“好吧!” 于是,三个毛头小子拿起灯笼,朝家里跑去。 时光过得好快,一下子飞过整整十年。 啊,十年光阴过去,弹指一挥间。 王斌、刘文亮和胡芝刚刚走到土坡前,他们一下子被惊呆了。 昔日“独龙岗”小饭馆,可怜一片焦土。 王斌叫嚷道:“这是怎么回事?” 胡芝嘶喊道:“这是为什么?” 刘文亮仰天怒吼:“这是谁干的?”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家乡唐洞的方向眺望,然而,被前面的一片棒子地挡住了视线。 刘文亮迫不及待地爬上一棵大树,骑在树杈上,手搭凉棚,往唐洞一望,大吃一惊,险些从大树上掉下来。 王斌问:“怎么了,文亮?” 胡芝问:“文亮,怎么了?” 刘文亮大哭,叫嚷道:“怎么了,怎么了,你们看看,到底怎么了?”他从大树上跳下来,急急匆匆往村里跑。 王斌和胡芝一起追着刘文亮,迅跑。 胡芝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斌问:“是呀,你怎么不说一声呀?” 当他们三个人跑到村口时,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手里横着龙头拐杖,将他们拦住。大喝一声:“站住,不许进庄!” 刘文亮问:“焦德昌大爷,怎么了?” 满头白发的焦德昌说:“我在这里等你们整整半天了,就担心你们会进庄!” 王斌急切地问:“那为什么?” 焦德昌老人说:“你们在这儿看不见,登高坡上看看,咱们村让小鬼子给糟蹋什么样子啦?” 胡芝问:“为什么?” 焦德昌说:“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 刘文亮说:“怎么是因为我们?” 焦德昌说:“咱村的伪保长焦让,怎么就知道你们仨当八路军去了,报告了驻扎在龙湾屯的小日本鬼子。结果,他们来了整整一个连,进村就把老百姓都驱赶到了老爷庙。挨个问:你们三个到哪里去了?问一个,不知道,挑死一个;问一个,不知道,挑死一个。呜呜——”他说到伤心处,实在忍不住,放声大哭。 刘文亮、王斌、胡芝齐声说:“走,咱们进村里看看!” 焦德昌只顾痛心疾首,却忘了提防这仨小伙子,追也追不上,撵又撵不着,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唇焦口燥呼不得,站在路旁,倚着手里的拐杖叹息。 刘文亮、王斌、胡芝最先跑到大庙前。 果然,大庙前的几排大青石上,血迹斑斑。 抬头一看,大庙的横梁上还吊着绳索。他们真想找个人问问清楚,可是,哪里去找人呀?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四周静得可怕。 刘文亮说:“咱们回家里看看吧?” 王斌、胡芝说:“好吧,那咱们就先到你家去,看看你的爹妈在哪里?” 于是,刘文亮、王斌、胡芝飞也似的朝刘文亮的家里跑去。 三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刘文亮家的小院。 正房的大门破损,门扇歪在一侧。刘文亮踹开门,叫道:“妈妈,妈妈——” 没有应。 王斌、胡芝齐声叫道:“刘大妈,刘大妈!” 依然没有人答应。 刘文亮、王斌、胡芝进了东屋搜寻,没有一个人影儿;又跑进西屋翻腾,仍然不见一个人影儿。 刘文亮急得干嚎:“妈妈,爸爸,爸爸,妈妈……” 三个人站在堂屋地上,面面相觑,想不出辙。 突然,刘文亮跑到东房山,弯下腰掀开扣在小窑洞上的破锅,大吃一惊。 原来他的妈妈爸爸都闷死在这里。 刘文亮“噗通”跪下,嚎啕大哭。 王斌说:“胡芝,去你家看看吧!” 胡芝说:“我们家在尽头,这儿离你的家近,先到你家看看去吧!” 说着,两个人一起跑开了。 远远地望见王斌家院子里的金丝小枣树,气喘吁吁跑近前,王斌踹开栅栏门,一眼望见爸爸在枣树上吊着。 王斌吓懵了,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半晌没有动弹一下。 胡芝愣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终于,胡芝拍拍王斌的肩膀,说:“王哥,别别……” 王斌终于扑倒在地,失声痛哭:“爸爸,爸爸——” 胡芝说:“找找你的妈妈吧!” 王斌站起来,慌手麻脚地四处乱翻,终于在西厢房里找到,老人家躺在地上,后背上留下一个大口子,棉袄被血水浸透了。 王斌蹦上院里的凉灶锅台,仰天怒吼:“小日本,我日你八辈儿祖宗!” 胡芝自然而然也想跑回自己的家里看看。于是,他放开脚步,朝家里飞奔。 家里没有一个人,东翻西找,也不见一个人的踪影。 胡芝慌了,欲哭无泪,干着急。 正在此刻,栅栏门开了。 胡芝回头一看,见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走进来。他一下子扑了过去,声嘶力竭地叫道:“爸爸,妈妈!” 老两口一个个张大嘴巴,问道:“咋,咋?” 巧极了,今儿前晌,胡芝的爸爸妈妈没有在家,是头天儿让嫁到柏树庄的闺女接走的,到闺女家过六月六去了。其实,上午小日本到唐洞扫荡的事,这老两口并不知道。 那么,儿子扑到他们的怀里,失声痛哭,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胡芝哭诉道:“小鬼子前晌儿,到咱们村扫荡,把王斌的爹娘都给杀死了,刘文亮的爸爸妈妈也让日本鬼子害死了!” 胡芝的爸爸胡崇德气得直哆嗦,声音发抖,问道:“是这样吗?怎么会,怎么会是这样?小鬼子也太欺负咱们中国人啦!” 胡芝噔噔跑进厢房,取出铡草刀,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叫道:“找小鬼子算账去!” 芝他娘死死地抱住儿子,哭叫道:“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胡崇德说:“你们几个不是一块儿参加八路军了吗?要报仇,找部队去,找韩贵德,他会有办法!” 胡芝说:“我、刘文亮和王斌,今儿头上午刚刚从军校回来,我们还没有到家,小鬼子已经从咱们村撤了,连我们几个也没有看见小鬼子的影子!” 胡崇德说:“儿子,先撂下铡刀,咱们把刘文亮和王斌找到一块儿,商量商量,找人家韩贵德,人家会不会管咱们这档子事!” 胡芝说:“打小鬼子是八路军份内事,管是得管,不过,同小鬼子作战,非同儿戏!” 胡崇德说:“那,那你娘看家,咱们爷儿俩,先去王斌家里去看看吧!” 胡芝扔下手里的铡刀片儿,说:“走!” 胡崇德和胡芝爷儿俩,一面气喘吁吁地走,一面看村子被小鬼子糟蹋的惨状。 唐洞村子并不大,只有三条土街。胡崇德和胡芝爷儿俩走到中街,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高高的白杨树下的那间小土屋被烧塌了,那是胡芝的当家子大伯胡崇礼的。 胡崇德和胡芝爷儿俩,急急忙忙走进院子,脚下满是灰烬。 胡芝正要往院子里探身,忽见高高的白杨树上吊着一个人,他不由得激灵一下子,浑身泛起鸡皮疙瘩,叫道:“爸,爸您看!” 胡崇德抬眼一看,吓个半死。半晌才缓过神儿来:“崇礼呀,你死得好惨呀!” 胡崇德和儿子一起,费劲巴拉地把胡崇礼从白杨树上卸下来,发现他的胸口上,肚子上,满是血窟窿。 胡崇德的眼窝里都是火,没有泪水,不哭,也不叫。 胡芝见爸爸气成这样,担心老人家挺不住,这才说:“走吧,先找到王斌和刘文亮再说!” 胡崇德不言语,慢慢站起,挪动着脚步,趿拉趿拉跟着儿子往外走。 胡崇德走着走着,被绊了一跤,幸亏儿子扶住,才没有跌倒。 胡芝搀扶着爸爸,一步一步往前走。 是的,孩子小的时候,是爸爸牵着儿子的手,学会走路;而今,儿子长大了,爸爸变老了,是儿子搀扶着老人,往前赶路。一代又一代,究竟往哪里去?茫茫然。 啊,还是走吧,那地方就在前面! 胡芝搀扶着爸爸,一步一步往前走,拐过了一条小胡同,突然,他们站住了。 原来,王斌和刘文亮正要去找胡芝,可巧在小胡同口遇上了。 王斌说:“胡大爷!” 刘文亮抱住胡崇德的腰,哭着说:“我,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呜呜——” 胡崇德哈下腰,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王斌的爸爸妈妈,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一个个都走了,倒把我这把老骨头剩下了,留在这个世上何用?”他呼天抢地,“天呀,老天爷啊,你咋就这样不睁眼睛啊!” 刘文亮说:“哪里有老天爷呀?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是不团结起来,一同跟小鬼子斗,把他们赶跑,那我们就休想过上一天消停日子!” 王斌说:“我们还是赶紧回部队去,向团首长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为乡亲们报仇!” 胡芝说:“回部队,咱们更得好好练兵,不然的话,报仇报仇,拿什么报仇呀!” 胡崇德说:“也别总指望八路军,八路军有八路军的事做,他们有他们的计划。依我看,每个村都该有自己的民兵,有自己的武装,村自为战,人自为战,能拿刀的拿刀,能拿枪的拿枪!” 胡芝说:“爸爸,您说的跟我们部队首长说得一模一样!” 胡崇德说:“可惜,爹上岁数了。不然的话,仨俩小鬼子,也未必能对付得了我!” 王斌说:“胡大爷,我们还是得赶紧回部队去,马上向团首长报告,再说,部队首长只允许我们一天假,回家看看。” 胡崇德说:“回什么家呀,一个个闹得无家可归了!”老人家说到这里,泪水涌满了眼窝,“走吧,走吧,部队上有纪律,这我清楚,赶紧回去吧!” 胡芝说:“爸爸,那我们就走了!” 王斌说:“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胡芝、王斌、刘文亮三个人,一步三回头,走了。 三个人出了村,又站在村头的黄土坡上,望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唐洞,一个个泪流满面。 数伏的天,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毒花花的日头当空照,眨眼之间,从西北的燕山缺口,涌来一堆乌云,像脱缰的野马,狂奔而至头顶,遮住了明晃晃的阳光。 王斌说:“要下雨!” 胡芝说:“暴风雨就要来了!” 刘文亮说:“这可咋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不淋个落汤鸡!”他的话音未落,铜钱大的雨点子便从空中砸下来,砸在脸上生疼。 胡芝说:“到大树下避避雨吧?” 王斌说:“你没听说,不能到大树下避雨,大树招雷电,咱们要是让雷给劈死,还怎么杀小鬼子给唐洞的乡亲们报仇雪恨了!” 刘文亮说:“那,那就顶风冒雨,一直往前跑!” 王斌说:“行!” 胡芝说:“行就行!” 唰唰唰,一道道闪电在眼前照。 轰隆隆,一声声雷声在头上轰。 雨点连成了雨线,雨线织成了雨幕,从天上到地下,白花花,雾蒙蒙,什么也看不清。 胡芝扯着嗓子喊:“还走吗?” 刘文亮嚷道:“当然得走,不走怎么行!” 王斌吼道:“对,当然得走,不走怎么行,走!” 三个年轻人,一面叫喊、一面顶风冒雨前行。 许是雷公感动了,许是闪母怜悯了,渐渐远去,大概跑到燕山的那边去了。 暴雨也突然停歇了。 红日拨散了乌云,明晃晃的,照得天上地下一片雪亮,眩惑着人们的眼睛。 王斌说:“落汤鸡什么样,咱们什么样!” 胡芝说:“不用天天洗澡了,得省多少事呀!” 刘文亮说:“反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能看见,咱们何不脱掉衣裤拧干了,晒晒再走?” 王斌说:“行!” 三个年轻人前后看看,确定没有来往行人,一个个脱掉衣裤,哗哗地拧水,抖开,晾晒在草丛顶上。赤裸裸地坐在光溜溜的地上,光着眼子闲聊。 王斌说:“你们说,是小鬼子可恨,还是日本狗腿子可恨?” 胡芝说:“依我看,还是小鬼子可恨。日本狗腿子,好歹还算中国人。” 刘文亮说:“分不出来谁可恨,谁不可恨,都可恨!” 王斌说:“你就说咱们村的伪保长焦让,你干吗非把咱们仨当八路军的事,报告给小鬼子,吃饱了撑的!” 胡芝说:“狗腿子,狗腿子嘛!” 刘文亮说:“焦让,你瞅他那相儿,歪戴帽,斜瞪眼,嘴里叼着洋烟卷儿,弯腰弓背蚯蚓腿儿,满口没牙瘪咕嘴儿,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王斌说:“咱也不是以貌取人。可我就是不明白,干吗好好中国人不当,当人家日本人的狗腿子!” 胡芝说:“狼走千里食肉,狗走万里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这玩意儿,见着阔人就摆尾儿,见着穷人就龇牙。” 刘文亮说:“焦让这类人,就跟狗一样,见着中国人就气势汹汹,见着日本人就点头哈腰。什么东西!” 王斌说:“你们还没说呢,到底是小鬼子可恨,还是焦让这类日本狗腿子可恨?” 胡芝说:“不用说,切糕换粽粽,一路货,没有一个好东西!” 刘文亮说:“依我看呀,日本狗腿子比小鬼子还可恨。这回,要不是焦让这类日本狗腿子告密,日本鬼子咋会在咱们唐洞杀了那么多老百姓?” 王斌说:“我说也是,像焦让这类日本人的狗腿子,说出状元榜来,也不能饶了他!” 胡芝说:“别聊了,这会儿,裤子褂子也都快晒干了,咱们还精光溜丢儿坐这儿聊票,要是碰见下地的老娘们儿,可咋好!” 刘文亮说:“那就穿衣服吧!” 王斌说:“好!” 三个年轻人,很快穿好衣裤,继续走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小路上。 冀东独立团作战室里,韩团长坐在太师椅上,眯着眼睛吸烟。 胡政委站在他的对面,说:“咱独立团的这一期培训班,情况还挺令人满意。” 韩团长说:“你注意到没有,顶数唐洞那三个新战士,留给我的印象最好,注意政治学习,军事训练还刻苦。” 胡政委说:“我看了他们的登记表了,这三个新战士都是唐洞的人,苦出身。” 韩团长说:“好苗子!” 胡政委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未来属于他们!” 韩团长从上衣兜里掏出怀表,看后说:“我就批准他们一天假,时候不早了,马上该归队了。” 胡政委透过西面的玻璃窗,意味深长地说:“西面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报告!” 胡政委高兴地说:“是他们,进来!” 果然是胡芝、王斌、刘文亮三个人。 韩团长站起来,问:“你们的家里怎么样?” 胡政委本以为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万没想到,他们三个人,一个个蔫头耷脑的,一声也不言语。 韩团长说:“怎么了,说话呀!” 突然,刘文亮“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王斌、胡芝也随着哭开了。 胡政委拍拍他们的肩膀,说:“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文亮哽咽半晌,抽抽搭搭地说:“日本鬼子到我们村里扫荡,我的爹娘都死了!” 王斌说:“我爸妈也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胡芝说:“我的爸妈可巧让我姐姐接走,倒是没有遇害,可是,我的当家子大伯,让小鬼子吊在树上,弄死了……” 三个人泣不成声。 胡政委说:“小鬼子又欠下中国人民一笔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 韩团长说:“估计又是驻扎在龙湾屯的龟田干的,这伙日本鬼子,在山里辛庄、焦庄户、唐洞一带,十分猖狂。咱们是该给这帮小鬼子点儿颜色看看了!” 胡政委说:“还是要帮助当地组织起民兵队伍,要是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每个村都建立起民兵组织,人人拿起刀枪,那力量可就大了,个把子小日本是不够打的!” 韩团长说:“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胡芝、王斌、刘文亮三个人,同时答道:“是!”转身而去。 韩贵德团长平日间,最喜欢看书,桌子上,枕头边,常常堆满了各色各样的书,《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另外,还从陈洪义那里借了一本《铁流》。《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这些回目,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平日聊票,也喜欢以这些书籍为题。然而,他并不喜欢《红楼梦》,他甚至说:“都说‘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都是瞎掰。《红楼梦》里写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一群哭哭啼啼的人,没劲!还是‘血溅鸳鸯楼’、‘拳打镇关西’解气,过瘾!” 为了读书的事,胡宝贤常常跟他争论。他总是说:“《红楼梦》是给有学问的人看的。老粗不喜欢《红楼梦》,这也很正常!” 韩团长说:“行了行了,我是个粗鲁人,你是个儒雅人。你读你的《红楼梦》,我看我的《水浒传》。” 胡政委哈哈大笑,说:“酒色财气,各有所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红黄蓝白,各好一色。你说好吃不过饺子,还就偏有人不喜欢吃饺子。谁也不能强求谁,是吧?” 韩团长说:“说真格的,陈洪义这本《铁流》,我想能不能在军校里传看一下。据说,苏联红军背着《铁流》作战!” 胡政委说:“当然可以!军校不止学军事技术,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军事技术当然要学,而且一定要学好,人人当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军事技术要靠人去掌握。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手里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韩团长说:“你这个团政委,我算服你了。砂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经你这么一说,我才懂得苏联红军为什么背着《铁流》作战。你能不能也给咱们团的战士写一部《铁流》那样的小说,背着你的书作战?” 胡政委说:“我不行,将来让陈洪义他们去写吧!我想,即使陈洪义不写,早晚也会有人去写,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股铁流。咱们的抗日战争,原本就是一场壮怀激烈的活剧,早早晚晚会有人来写,况且,一部书远远不够,至少要写出十部八部、百八十部来!” 韩团长忽然扭转话题,说:“说点儿现实的,平日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有些欠缺,应该改为‘练兵千日,用兵一时’。兵,咋能养?要练,把兵练得棒棒的,战时,才能拉得出,攻得上,打得胜。光养,吃得好,睡得好,养得白胖白胖的,一个个像一头头肥猪,到时候还能打仗?门儿也没有!” 胡政委说:“这话对,有道理!咱们办军校,既练兵,又练思想。就是要让战士们憋得‘嗷嗷’叫,感到没有仗打,浑身痒痒,不舒服,不自在。这样的部队才是最棒的,不可战胜的!” 韩团长说:“我读《三国演义》,让我最感失望的就是‘马谡失街亭’。诸葛亮平生谨慎用事,可是,在选择谁去镇守街亭这件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失策,常常令我为之扼腕。诸葛亮明明知道马谡这人虽熟读兵法,深通谋略,但他意气甚高,骄傲自满,只是由于当时马谡奋力争先,且立下‘军令状’,诸葛亮就决定马谡去担当镇守街亭的重任,结果落得街亭失守,挥泪斩马谡。每次读到这里,我既恨马谡,又心疼马谡;既为诸葛亮惋惜,又为诸葛亮叹息。我常常想,我们作为八路军的指挥员,既不能犯马谡那样的错误,又不能出现诸葛亮那样的失误,反胜为败,造成损失。” 胡政委说:“其实,我们的军校里的课程,完全可以充实一些这样的内容,形象生动,活跃气氛,省得都是些干巴巴的教条。” 韩团长说:“要么这样,结合战例,你给大家讲《红楼梦》……” 胡政委哈哈大笑:“《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婆婆妈妈的事、哭哭啼啼的人。有什么战例可讲的呀!不过,我可以讲讲《铁流》,讲一讲八路军战士怎样在部队中锻炼成长。” 韩团长说:“好好,这样可以使战士们开阔眼界,不光是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要跟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胡政委说:“你可以结合《水浒传》里的许多战例,讲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像‘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宋江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第三次攻打祝家庄就打胜了?这里就有很多作战知识可以传授。” 韩团长说:“我想:这些理论上的课程,还是由你来担任。我就负责军事训练,像狙击手、大刀队、神炮手的训练,都由我包干了,怎么样?” 胡政委说:“知人善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哈哈……” 满头白发的焦德昌,拄着拐杖,气喘吁吁地往村里走,累了,乏了,坐在老槐树下喘会儿气儿,刚刚坐下,对面来了一个人。 那个人走到他的对面,站住了,说:“八叔,老八叔!” 焦德昌慢慢挑起眼皮,问:“你是谁?” 来者说:“八叔,老八叔!真老了,咋的?我是焦让,这老爷子,耳聋,眼也不好使了?” 焦德昌说:“嗷,焦让呀,咋着,又去龙湾屯勾结小日本儿去?那就快去,别耽误了你的事!” 焦让说:“八叔,我的老八叔!您说什么呢?哪里的话,那些缺德带冒烟的事,找不着咱爷们儿!” 焦德昌说:“你也甭变着法子蒙我,我也不是瞎子,聋子,我看得见,听得见。我可告诉你,你姓焦,我也姓焦,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那些给祖宗脸上抹灰的事,你就怎么干得出!” 焦让说:“八叔,老八叔!您真是老糊涂了,还用往上捯五百年吗?咱们两家子刚刚出五服,您比我的亲叔叔能差多少呀!” 焦德昌说:“你也用不着跟我套近乎,唐洞村的老焦家,出了你这么个汉奸,都没脸见人呀!” 焦让说:“这是什么话!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好像龙湾屯的日本驻军是我引进来的!大日本皇军长胳膊长腿,他们要去哪里,我能管得着,关我屁事!” 焦德昌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焦让说:“您说老半天,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倒是句实话!” 焦德昌说:“那我问你:刘文亮、王斌、焦芝,这几个孩子当八路军的事,到底是谁报告给小鬼子的?” 焦让装出惊讶的样子,说:“这仨孩子当八路军啦?您要不说,我连影儿都不知道!” 焦德昌说:“快去吧,去告诉你的日本爹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快去吧!” 焦让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您都不信呀!”一面说,一面甩手走了。 焦德昌抡起手中拐棍儿,冲着焦让出走的方向,大声说:“当心,天打五雷轰!” 果然,一堆堆乌云从燕山的那一面,滚滚而来,一忽儿,便把明晃晃的太阳遮住了。 焦德昌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拐杖,直指高天,声嘶力竭地高喊:“老天爷,显灵了!显灵了!” 几乎是在焦德昌叫喊的同时,“呼拉拉”一道闪电,大地一片亮光,“轰隆隆”一声炸雷,震耳欲聋。紧接着,铜钱似的雨点子,“噼噼啪啪”砸了下来。 焦德昌拄着拐杖,一面踉踉跄跄地走,一面高声嚎叫:“老天爷,睁睁眼吧,打几个霹雷,照准小鬼子的脑袋,狠狠地劈!” “哗哗啦啦”,大雨倾盆,像是从天而降。 焦德昌一路东倒西歪,连滚带爬,回到家里,早已成了落汤鸡。他急急忙忙脱下湿衣服,哆哆嗦嗦爬上炕。往外一看,从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织成白亮亮的雨帘,院子里白花花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焦德昌喃喃地说:“也许,老天爷真的睁眼了。这么说,小日本的日子,长远不了啦!” 王克臣(男),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会员,《希望》主编。自年,相继出版小说集《心曲》《生活》、散文集《心灵的春水》《春华秋实》、随笔集《播撒文学的种子》、杂文集《迅风杂文》、报告文学集《潮白河儿女》和长篇小说《风雨故园》《寒凝大地》《朱墨春山》。《心曲》是顺义第一本文学作品集,曾在北京市第三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及上海书市展出;报告文学《中国好儿女》获北京市“五一工程奖”;《风雨故园》获全国“长篇小说金奖”、北京市“苍生杯”特等奖;《寒凝大地》获首届“浩然文学奖”。年,作者荣获首届全国“百姓金口碑”;年,授予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年,获北京市辅导群众创作“终身成就奖”;年,获第三届京津冀“文学创作银发达人奖”。 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zz/8245.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千零一个愿望一
- 下一篇文章: 官方服务入口健康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