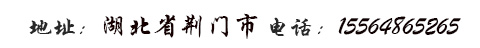十四岁,我以处子之身,成了风满楼头牌
|
您看此文用 ·秒,转发只需1秒呦~ 1.书名:头牌小艾 2.章节:49章完结 3.大小:KB 4.售价:3.99 正文 文案 十四岁,我以处子之身,成了风满楼头牌 十五岁,我拐了只金猪,脱了贱籍,开始了我的实习仵作生涯 仵作这职业,真是非常有前途 我第一次看到三具尸体在我面前OOXX, 我第一次知道缢死者会遗精脱粪, 我第一次了解,原来女体盛是仵作发明的工作餐的变种, 我第一次懂得,原来人是可以戴面具生活的 我是头牌,我叫小艾 主角:小艾,墨让,吴越┃配角:南平,夏至┃其它:头牌 类型:原创一般架空历史爱情 作品风格:轻松 第一章头牌的彪捍生活 我叫小艾,听妈妈说,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咱的第一声发音是“哎”。 不要问我姓什么,因为我是弃婴。哈,麻烦您收起您那同情的眼神,像我们这种入了贱籍的人,没有姓,实在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人家说,风满楼成了八街九巷烟花地的第一楼,不是因为有京城第一艳妓柳扶风,也不是因为有彪悍婀娜风韵犹存的花叠翠花妈妈坐镇,而是因为有我头牌小艾。 嘿,您别不信,虽然我家花妈妈曾经给了我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语:“这孩子,五官分开看,两个字,普通。合起来看,也没见有什么别样的风韵,还是老老实实的普通着。”但是咱仍旧是头牌中的头牌,八街九巷头号递牌子的头牌,小艾! 咱能承各位姐儿不弃,得了个头牌的名儿,全凭咱生就了一双剧毒无比眼睛。只要从客人进门到被我带入厢房这段短短时间,咱就能把他的职业喜好摸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姑娘们投其所好,自然是事半功倍,客似云来,生意兴隆,恭喜发财,并贺新年。 说白了,我的存在,就是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人家也叫干我们这行的为龟公,或者大茶壶。 嘿,谁说女孩子就不能做龟公了?俗话说的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啥行业干到极致,都能出极品。 去年,咱以十四岁妙龄,荣登八街九巷烟花地“最推动生意兴隆人物”宝座,要知道,以前可都是各届花魁当选,从无例外的啊!这充分说明,咱大茶壶也有春天。 说的多么辉煌轻巧,其实咱背后也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咱有意来抱怨啥,咱生就了一个贱籍的身份,还能指望别人对咱多好了么?甭管您心里头咋想的,为了咱家花妈妈的生意考虑,有人扇了咱的左脸,咱也得把右脸陪着笑凑上去,哪位大象把咱踩成了二维的,咱也得记着把芳香留在大象大人的鞋底。 不过……嘿嘿嘿……对不住对不住,咱一个没忍住,嘿嘿嘿…… “怦怦怦!”咱一个机灵,看到对面坐的那尊冷面菩萨,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哎哎,不瞒您说,咱堂堂一头牌,见了花大娘,就成了块面疙瘩,任她捏扁揉圆了。比如现在。 花大娘敲着桌上的银锭,怦怦怦,怦怦怦。 斜着眼看着我:“说吧,这字据,还有那外头候着的家伙,都是怎么回事?别告诉我,你茶壶不做,改做姐儿了?”冷笑冷笑,笑得咱习惯性肝颤。 “那个……”挠头,顾左右,不敢言他。 “说!”花大娘狮吼功上阵,我立刻缴械:“是是是是这样的!……” “大娘您还记得大概一个月来的那三个官府的人么?” “就是那三个便装的捕快?”花大娘不愧为过目不忘、文成武德的前前花魁,凝神细想片刻,就给出了准确答案。 点头:“没错,就是过来拐弯抹角地查失踪姐儿的那三个。” 妈妈杏眼一瞪:“那跟墨家二公子有什么关系!你小子少跟我扯皮!” 妈呀,吓死我了。眼睛大了虽然秋波送得动人,可生起气来也格外吓人,那眼珠子跟要掉出来似的。看她脸皮翻书一样翻了十几年,咱还是习惯不了。 抖抖索索地陪着笑:“就是,就是……” 其实这话说起来也简单。在这花街,又有哪个不想脱了这贱籍呢?可我堂堂,啊不,区区一个大茶壶,虽然是个名壶,月钱稀少、打赏凭天,又能存得下什么钱来?花妈妈可以不要我赎身的钱,可是由贱籍改良民的银子呢?关系呢?除了走些歪门邪道,把主意打到出入花街的大人物身上,咱还能有什么办法? 面前这位爷二十出头,眼亮若星,宽袍大袖,牙白的衣裳翩若流云,风流倜傥,端的是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 他张大了桃花眼,看看我,又看看门外,再看看我,复又看看门外。轻咳:“这位小哥,我要找的是姑娘。” 我顺势坐下,拧肩,抛了个夸张无比的媚眼过去:“这位爷,我就是八街九巷的头牌啊!” 满意地看到他生生吞下茶水的狼狈样子,偷笑:嘿嘿,咱也没骗你啊! 这位爷在我电眼下败下阵来:“那麻烦小哥,替我找位姑娘来。” 妈的。 老娘我对天发誓,咱已经发育了。而且咱的声音,虽称不上天籁,也是黄莺出谷吧? 我恶狠狠地凑近他,压低声音:“墨让墨二爷,您今天想替哪位姑娘赎身啊?” 墨让微向后仰,避开我如兰的哈气:“这位小哥,我第一次来,你恐怕认错人了。” 认错?那一闪而过的紧张神色,怎么可能逃过我小艾的毒眼? 咱在打算敲诈前,早就把八街九巷出现失踪姐儿的大小青楼逛了个遍,失踪的姐儿多大年纪,失踪前几日接了什么客人,可有什么老相好儿……一共一十三位姐儿,咱记录的纸就用了八十三张,排除了三个可疑人物,咱又远远留意了墨让好几天,直到又有位姐儿失了踪,咱才算锁定了目标。前前后后花了咱近一个月时间,咱能认错? 悠哉游哉地替自己沏了杯茶,哧溜哧溜喝得嘹亮雄浑:“本姑娘可能认错人,但衙门的捕头大哥不可能认错的吧?” 他啪地甩开扇子,飞速扇着风:“捕快,呵呵,捕快就更加不可能跟在下有关系了。” “是啊是啊,”我笑眯眯地接腔,“不过他们对各个楼里姐儿们的失踪,很是感兴趣哦!” 墨公子擦汗:“哦?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啊!”撑着头故作天真,“听说这些姐儿失踪前都接待过那位墨公子呢!不过想那墨公子一介书生,应该不会犯下什么案子吧?” 墨公子忙不迭点头:“是是是。” “不过,”我话锋一转,奸笑着看他愣住,“听说墨公子家教甚严,这位爷你说,要是让墨公子那位做盐运生意的严肃大哥,知道墨公子和几位姐儿有染的事情,那该如何是好啊!”做作地叹着气。 他一拍桌子,舍生取义状:“敞开天窗说吧,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原样拍回去:“替我赎身,帮我脱贱籍,找个落脚地,还有份像样的工作。没了。” 他楞住:“这么简单?” 靠,你大爷的。你有个做盐运的大哥,家里财产不知凡几,自己不过是个闲没事就爱鼓捣些奇门遁甲,四书五经不会,歪门邪道都懂的二世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可是我们这些被困在烟花地的人一辈子的梦想啊! 二世祖极慷慨地甩出一沓银票:“一千两够不够?“ 我热泪盈眶:你大爷的,拿钱砸我…… 来吧来吧,砸死我吧。 辨认过银票真伪后,我眉开眼笑:“为免反悔,咱来立个字据,一式两份,按约履行,事毕作废。”嘴上说着话,手上不停,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合约半成品,填好具体条款,签上自己大名,递给他。 他依样在乙方那栏签上自己名字,嘴里赞了句:“没想到你字写得倒很秀丽。” 废话,你以为各位小姐给恩客们的情书,都是自己写的? 他不情愿地起身,又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墨让的?” 你当我傻啊?不调查清楚就敢和人签字据? 这些,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只笑眯眯的盯着他看,一边放着眼刀一边感慨,小样长得真好看啊,鼻梁挺直眉如螺黛,小麦色的皮肤这么近也看不到个汗毛孔,嘴唇竟然敢是粉红色,还是水水嫩嫩的那种。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老天爷,我这都快成沙漠了!你为啥要把如此美貌赐给一个男人啊,真他妈的浪费。 美男在我如狼似虎的眼光中败下阵来,狼狈偏过头,不再追问。 花大娘常说我长了双鬼眼,被看久了,就像身上衣服一件件被我眼刀剥去。 我笑,感情那些恩客便都渴望有我这样的一双眼了。 吹着口哨收起银票和字据,惋惜:唉,这么蠢这么有钱又这么好看的男人哪找啊,真想以身相许了。 “所以你被人拿银子砸了,就来拿银子砸我了,是不是,小子?”花大娘听我麻利地叙述完,将银子重重在桌上一磕,掮肩冷笑道,“好你啊,姐儿们有事儿你竟不先告诉我,竟敢自顾自的敲竹杠?小子,你啥时候这么有主意了?”花大娘的后槽牙死死磕着,说话时不时咯吱咯吱作响,听得咱的寒毛那叫一个激动。 我狗腿地陪笑,不忘替我自己和那金猪二世祖正名:“哪能呢妈妈,咱也是打探过的,姐儿们只是不再在花街了,想那墨二公子应该没做什么恶事,大不了是圈起来养着了。”又排出十张百两面额的银票,“大娘,这是小艾我的赎身钱。” 花大娘那重峦叠翠的脸抖了抖,神色几次变化,最后呈现出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总算把你这祸害送走了,好过再浪费我的米钱。” 我深情地:“大娘,我知道你从小就疼我,拉扯我长大,还给我取名字……” 大娘笑骂:“谁用心给你取名了?不过是看你第一声发了个什么音罢了,要是你当时哇哇大哭,现在就叫娃子了。” 黑线,再接再厉:“我长到十五岁,你也不提让我卖身的事。” 大娘起身捏住我脸皮:“就你这怂样儿,卖也得卖得出去啊!” 我沉默,怪叫:“花老妖,老娘好不容易想营造个正经的离别气氛,你干嘛老拆我台?” 花老妖彩帕招摇,妩媚地笑:“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伤感嘛!”尾音上扬,可惜最后被一个颤音破了功。 我也笑:“大娘,眼线都糊掉了!你眼里是出汗不是?” 花老妖恼羞成怒,大脚踹过来:“滚吧滚吧,赶紧滚,别让老娘再看见你!” 门开,我的包裹我的人伴着我的卖身契一起被丢出。靠,这动作也太快了!我爬起,不理一旁墨让惊讶的目光,跳着脚骂:“花叠翠,你这千年老妖,这么快就给咱收拾好了,是不是早想着赶老娘走呢?咱跟你十五年,你怎么就不带留咱一句的?咱想着盼着想出了这窝儿,也不全是为了自个儿!就算是为了自个儿的前程,也不带你这么绝情的!养条狗养十几年也有感情了吧?你咋不想想,老娘要是走了,谁天天给你熬醒酒汤,谁晚上帮你暖床,你要是再浑身骨头疼,谁能连着十二个时辰不住手的替你按摩?” 骂着骂着,我也哭了。妈的,我也忘不了,是谁收留我教我读书识字,是谁喝醉了就拉着我呜呜地哭,叫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是谁在变态恩客非要为我开苞时拦着挡着,拼得被打断了一根指骨,到现在右手无名指都不能伸直。 墨让这小子在一边兀自栝噪,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我擦干眼泪,在生人面前,我永远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笑,越伤心,笑得便越灿烂。望着我的金猪,我问:“去哪?” 这小子忽然就笑得很奸诈:“去一个很适合你的地方。” 作者有话要说: 终于开文了,热泪盈眶ing 知道大家都想养肥了看,算了,这孤独的头几天,就留俺一个人在坑底孤独的撒土吧…… 第二章 衬着晨光熹微,天地间仍然像笼了道蓝纱,朦朦胧胧的只见眼前青瓦幽幽,墨竹掩映,层层叠叠的各色植物分隔出各个区域,桃红柳绿,海棠芭蕉都被刷了层淡淡的紫,挤挤挨挨着沉默的伫立。汉白玉的地灯笼里尚有残留的灯火,被似有似无的晨风吹得明明灭灭。青色的石板路在宽叶窄藤的遮挡下,含蓄地延伸湮没在一片墨样的浓绿中。 抬头,依稀可见正对的主宅上一块大大的匾额,“无月小筑”四个黑字,似乎是因为光线不足,黑色的线条不住扩大,渐渐的黑成一团。 天,看这规模,这哪是座宅子,分明是座园子。 苦哈哈地回头扮可怜:“二爷,您带我赶了半晚的路,就是到这里来拜师的?” 墨让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啊?啊!对!” “那为啥不进去等啊?爷,您真的跟我的未来师傅很熟么?” 墨让有气无力地靠在外墙上,死猪状:“你进去试试看?” 什么?叫咱试试看?这里一定有猫腻儿!咱还是小心使得万年船,堂堂一头牌,别在这阴沟里翻了船,嘿嘿,虽说这阴沟挺华丽。 仔细看一看,嗯,没有影壁,竟然能从大门直接看到主宅的门扇,这……这还真挺不正常的。随手捡了块石头,扔向青石路。 石子在石板上撞击,声音清脆,啪,啪啪。 胆战心惊地等了又等,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哎? 想了又想,还是没敢迈出小小的第一步,跑过去推推昏昏欲睡的某人,低声下气:“爷,您打算让咱啥时候拜师啊?” 墨让使劲揉揉桃花眼,力道之大,看得咱那叫一心疼。哎哟我的爷啊,咱今天才知道啥叫暴殄天物,老天爷,您赶紧赏道雷劈死这个不知惜福的混蛋吧! 可惜老天爷耳朵有点背,人家兀自揉得开心快活,末了红着一双兔眼问我:“什么时辰了?” 抬头看天,残月如同身边这位活宝,死气白赖地趴在西边山头:“寅时了吧!” 墨让整个人都贴在了墙上,软塌塌得好似要融化:“快了快了,还好来得及!” 快什么?来得及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问出口,就觉得身边嗖的一道风吹过,伴随着几声闷哼,回头,墨让这厮已经趴在了地上,脸色倒是比刚才红润了许多,愁眉苦脸:“死祸害,你又偷袭人家!”末尾那微妙的上扬带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恶……您怎么不再翘个兰花指?嘁,您这不明摆着跟我们姐儿抢饭碗么?不过,这厮在说谁? “你这厮,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这次想来干嘛?”慵懒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啪地转头,找寻这迷人的发声源。 娘诶,原来神仙是这个样子的。 月白色的衣衫,有熹微的晨光和西斜的白月做背景,及腰的长发竟然泛着幽蓝的光,狭长的凤眼,半抿的薄唇,本就十分出色的相貌,配了一身清冷又微带邪魅的气质,显出亦正亦邪的风姿来。即使他现在半卧在矮墙上,仍像躺在华丽的睡塌上般惬意。 墨让敲敲我的大头,声音好像十分不爽:“瞧你那样儿!这是你未来师父,吴越。口天吴,走戊越,这祸害最喜欢逛烟花地了,一肚子坏水。小心你被玩死了,还帮忙递刀子!” 哦,无月吴越,好名字!二世祖是气神仙抢了他风头?嘁,公孔雀!我装出副口水滴滴的样子,嬉皮笑脸:“师父麾下死,做鬼也风流!” 吴越喷笑,冲我眨眨眼,飞了个赞许的眼神过来,似是十分赞同我的恶作剧。 嗯,脸上有点热……一定是晚上赶路吹多了凉风,该死该死。 “祸害,她就交给你了,我回去了!”墨让打着哈欠,口齿不清地说。 “等等,虽然是你这家伙带来的,可也得过了我的三关,才能正式收作徒弟。”神仙依旧是人畜无害的模样,吐出来的话却怎么听怎么冷血。 墨让摆摆手,擦去刚刚眼角挤出的几滴泪:“别玩了,你那三关就从来没有人全部通过过,就你那小徒弟南平,不也是没过第三关么?” 神仙打了个哈哈:“我不管,反正不过我就不收。” 哈,果然冷血。 墨让又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哈欠个暴殄天物的混蛋玩意:“我也不管,反正我要回去睡觉了,要是她过不了,就先寄存在你那,等我有空了再来取。”又贴近我,悄声道,“不算违约吧?”讪笑,“反正你也挺愿意跟他住一块儿不是?” 去你的,美男再有魅力,也大不过前途!你这家伙让我在这穷耗着,很有意思? 还寄存?你爷爷的。 不理我恶狠狠的眼刀,二世祖潇洒的转身,摆手告别,一晃三摇,不过一刻便出了我视野范围。 死墨让,来的路上像蜗牛,走的时候怎么那么快! 转头,我陪笑:“师父,咱啥时候开考啊?” 神仙收了笑容,斜睨我一眼,万种风情瞬间化成皑皑冰雪,连说话的音儿都带着冰渣子:“不用这么早叫师父,你不一定过得了我的三关考验。” 不由打了个寒战。啧啧,吴神仙,您是四川人吧?这变脸的绝活使得真地道啊! 神仙飘下矮墙,带着我走进园子:“跟着我,别丢了。” 啥?这还能丢了?偷偷回头,妈呀,见鬼了。原本坦荡的石板路竟然倏地隐在的花丛中,不知是什么花草的枝节直愣愣的斜支着,衬着青灰的天空,颜色愈发的暗沉,只能看得出瘦骨嶙峋的轮廓,随着咱和神仙脚步向前,那花枝也沉默着后退,默默交叠又默默分开,看得咱眼花缭乱,有种花移草动的错觉。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古怪阵法吧?桃花阵?八卦阵?忙转头跟上神仙的脚步,小心记忆所经过的路线。桃花向前走三步,海棠左转…… 神仙大喇喇在堂上一坐,扬声:“南平,找五个人上来!”转头冲我一笑,花开月徘徊,影动云纷乱。咳,抱歉抱歉,为姐儿们写情书的后遗症。 神仙偏着头看我,笑得风情万种:“猜出这五个人干什么来,就算你过关。” 嘿,咱的老本行啊!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压抑住喜色,故作为难状:“神仙大人,这太难了吧?打个商量,三个人如何?” 神仙面色一冷,一对儿墨蓝色的眸子仿佛带了寒霜,冰得我双腿发软,口齿不清:“三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嘿嘿,咱哪能搞特殊啊!神仙大人,您说对不?” 身上那难挨的麻冷总算减轻了些,我松了一口气,嘿,在神仙面前,还是少耍些花招吧! 过了大半个时辰,站得我头晕眼花,才算是盼来了这五个人。 脚步匆匆,为首的是一名面相讨喜的青年男子,二十岁上下,步履轻快,衣衫整洁,袖管挽到肘部的位置,冲着神仙与我羞涩一笑,便站在了堂角。 跟着那青年的是一个面有微须,书生模样的中年人,双手拢在袖中,眼帘低垂,亦步亦趋,看那青年人站下,便也诺诺站在一边,低头涵胸。 第三个进来的是个曲线玲珑的少妇,袖管和裙摆都有大量细碎褶皱的痕迹,眉目张扬,嘴角带笑。 接下来是位中年男子,三十岁上下,脸色蜡黄,没精打采,病怏怏的样子。双手过膝,指节粗大。 后面的……咦,后面的人呢? “别找了。”神仙开口,瘫在太师椅上,华丽得不像话,“第五个,是我。” 我屁颠屁颠跑到为首青年面前,拱手陪笑:“这位小哥儿好!” 那青年笑了笑,看了看神仙,没有答话。 我继续扯出最灿烂的笑:“小哥,不说话也行,可否容咱看看您的手相?” 青年又看了看神仙,才算伸出了双手,摊给我看。 我笑呵呵摸过他双手,又摸遍了余下三人的手掌,才跑到神仙近前。神仙挑了挑凤眼:“怎么,我的也要摸?” 口水滴滴,拼命点头,淫笑着伸出双手:“您要是愿意,摸我的也成啊?” 神仙嫌恶地拍掉我的爪子:“看完没?看完就说!” 吓得一缩脖子,点头,是是是,您老已荣登与花妈妈齐名的小艾最怕之榜首。 手指向那少妇,竹筒倒豆子一般: “这位姐姐生得好俊俏,利落行装,袖管有高卷过的痕迹,鞋面上袖口上都沾了污水的印迹,咱心里第一印象,自然是厨娘了。然而若姐姐是厨娘的话,这扎起裙摆的动作,倒是少见了。还有姐姐脸上那掩不住的英气,人都说相由心生,这股子英气,定然不可能在镇日与锅铲为伍的厨娘脸上找到的。” “况且刚才咱到这姐姐近前,却没有闻到半点油烟气,再仔细看姐姐裙上,有些被火星子燎到的微小洞眼。还有呢,就是姐姐双手掌心都有老茧,刚才咱得罪,捏了下姐姐的小臂,那肌肉结实得,跟铁似的。这样看来,姐姐其实是个铁匠吧?” 少妇微笑点头:“想不到妹子如此好眼力!”退后一步,显是十分满意我的答案。 我笑,转向那中年文士: “这位先生一看便是位读书人,然而进退得宜,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三指的指腹有茧,想是长年拨打算盘所致,先生该是位账房吧?” 那文士也拱了拱手,默然退后一步。 “至于这位小哥……”我眼睛一转,看向那青年。 “小哥身上味道很杂,既有股子油烟味,又能隐约闻着些冷香的味道,小哥必然不是普通的小厮。听神仙大人刚才唤南平,而小哥引着三人出来,更几次看神仙大人反应方敢动作,咱猜,小哥该是神仙大人唯一的徒弟,南平吧?” 南平尴尬地一笑,也退后一步。 “这位爷就比较有意思了。”我转向那中年男子,陪笑。 “这位爷虽面色蜡黄,但眼中精光四射,双手皮肤粗糙,四指长度相差不多,咱听说,打小练外家掌法的高手手掌,就是这副模样。咱虽然不敢断言,也能拍个胸脯,爷您是个练家子。看爷您一脸正气,咱斗胆猜一句,爷您该是个捕快吧?” 那中年男子一脸惊愕,拱手:“小姑娘有见识,郑某佩服!”也退后一步。 嘿嘿,咱虽然是头牌,但咱不是神人。咱能辨出来老郑是个捕快,全因为他就是前几天便衣来风满楼查姐儿失踪缘由的三捕快之首。他们当时忘了换掉官靴,如今,倒便宜了我这头牌。 转身,看向神仙大人。 “这么早,大人您就能支使徒弟唤动衙门公差,来帮您做个小小的测试,大人您和衙门的关系,必定非比寻常。” “咱对衙门的情况并不熟悉,咱只知道,除了县太爷之外,衙门的职业大抵不过是捕快、师爷、仵作三种,大人必定起了一种作用。大人丰神俊朗,潇洒不羁,实在不像是须得天天在衙门候着的捕快。再加大人宅内奇门遁甲层出不穷,连进门道路都蕴含玄机,咱本该猜大人是衙门的智囊,也合了大人出尘的气质。但大人刚刚拂开我时,带出了极细微的一股子皂角和醋的味道,咱虽然不甚明白,但也知道若是光动脑筋的活计,依大人的品味,是必然是不会轻易沾上这些廉价的味道的。再者,墨二少叫我这小人物来学的,若真个是光动脑筋就解决的,咱反而要发愁了。因此咱讨打的猜一句,大人,是做仵作的活计。” 说完,我屏息凝神,躬身等着神仙大人给我答复。 刺骨的冷意陡然压向我又陡然消失,神仙哧地一声轻笑:“第二关。” 呼!浑身肌肉一条条爆开,我好像个松散的拖把。 南平引我进入里屋,唇不动,轻声:“别高兴得太早,这一关,很难。” 第三章 第三章南平燃起一柱线香:“一炷香之内,开门解锁,就算你过关。” 我笑:“多谢!” 南平欲言又止,最后只叮嘱一句:“收敛心神。” 我真心实意地笑:“多谢!”又有些好奇问道,“小哥何以对我如此照顾?”实话说,咱离我见犹怜差得还真不只一点半点,萍水相逢的,我还真不觉得自己那么可人疼。 南平赧然:“有个特别的小师妹,也不错。” 呵!谢谢南平,谢谢你。原来除了花妈妈,还有人相信咱是特别的,对咱另眼相看。士为知己者死,我小艾,为了您老这句话,拼了! 南平撞上门,随着他的撞击,金色的大小齿轮带着颗颗滚珠悠悠转动,一根巨大的门闩伴着嘎嘎声响缓缓伸出,将门顶住。 傻眼,这少说也有二十多个齿轮,怎么解啊? 哀号,大哥,您好歹也给我提个醒儿啊!这跟老虎吃天一样,叫咱咋个下嘴啊! 借着室内十几根蜡烛的光芒慢慢摸索,从门闩渐渐向外,终于顺出七个终端齿轮,大大小小,齿轮上各带了一个奇形怪状的表盘,大概就是要从这些表盘下手了。叹气,认命地看向第一个齿轮。 九个点三三排列,沟槽纵横斜划,外插了根金属圆棒,半根露在外面,泛着圆润的黄色光芒。表盘边刻了一行小字“九星连珠”?什么意思?是说要划过九个点么?试着转了下金属棒,沿着外围八个点转了一圈,又转回半个边,划过中间的点,放手,等待。 金属棍咔咔移回了起点,露在外面的棒身比原来短了一半。 冷汗,不能重复路径?而且还有次数限制? 不敢再乱试,手指沿着路径画了好久,才自信满满地握住小棍,划出了个十字弓形。 门闩咔咔作响,向后退了一分的距离,正好是卡住门的长度的七分之一。 不由大喜,转而看向第二个齿轮。 横竖大小不一的按键组成了迷宫一般的表盘,上方一根铁管中坠了三颗钢珠,边上有一根木柄,扳下手柄,第一颗小球被放出,骨碌碌在几块按键上弹射一番,落入了下方洞中。 懵懵懂懂地按下小球撞击的第一个按键,按键被压下后维持了原来的位置,似乎是对的?接连按下被弹射过的按键,却在三分之二的位置按错了一键,按键全部归位。 妈妈啊…… 再次扳动手柄,落下第二枚钢珠,路径竟和方才完全不同,咱没辄了,只得死记硬背,总算过了这一关,门闩再向后退一格。 第三个表盘与第二个类似,不过是变成了记忆活字版中突起偏旁的位置和顺序,门闩再向后退一格。 第四个,第五个…… 莫非这一关便是考校记忆力的?这倒也说得通南平的那句“收敛心神”。 第六个表盘看起来有些熟悉,再在脑中仔细过一遍,竟然是园子里路径的阵法图。 这是谁设计的混蛋狗屁关卡?教人死记硬背了四五个路线图之后,又考校人进门的路线,这不是纯属难为人么?嘴里骂骂咧咧,也不得不收敛了心神,凝神细想来时的路径。 桃花……海棠……唉,这十字弓来凑什么热闹! 柳树……芭蕉……嘿,怎么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偏旁部首? 再细想下去,这些红桃绿柳竟好像长了脚似的,忽忽地围着我转动起来,其中还夹杂了大大小小的十字弓、冰狠冷硬的残缺字符,诡异地变幻着阵型,呼啸着向我袭来。 “不,不要了,不要了,求求你。” 什么声音,这么熟悉?这是谁的声音?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这究竟是谁的声音,这么的撕心裂肺,悲惨绝望? “花妈妈,我做了个噩梦……” 奶声奶气的呓语,带着浓重的鼻音,似乎刚刚哭着惊醒。这是儿时的自己么?咱竟然也这么脆弱过?咱到底做过什么噩梦? “小艾,答应我!答应我!不管怎么样,就算食不果腹,也要脱了这该死的贱籍,就算为了我,也得活出个恣意的人生来!” 这一遍遍的嘱咐,这般绝望又饱含着希望的醉话,不是花妈妈又是谁?那个用铅华埋葬青春,又用铅华粉饰青春的花妈妈,她将青春的梦想和期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啊! 这样想着,心脏突然一阵抽痛,令我陡然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瘫在地上,眼前仍重叠着各种汉字与十字弓,那些偏旁歪歪扭扭的堆在一起,竟组成了杀、仇、伤一些个血腥的字眼,不断在我面前飘荡,无声鼓噪着我,我双耳被沸腾热血鼓荡得卜卜作响,头疼欲裂,想大叫,想挥舞拳头,想噬咬些什么,想尝到鲜血的滋味。 狠了狠心,一口咬上自己左臂,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弥漫了我的口腔,妈的,真咸,出去要多喝点水了。 也许是血放得有点多,也许是连夜赶路又累又饿,我终于觉着些虚弱,觉着累,觉着蕴在肌肉里的无穷的气劲一点点化作了酸软,那汩汩冲刷着我耳膜的血液终于平缓下来,那没处发泄的精力终于渐渐离我而去,心思终于可以不受蛊惑,逐渐沉淀下来,将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开锁上,眼花了就咬一口,终于在咱咬了三口就快咬掉一块肉时,门开了。 转身,那柱香还有不到半分的长度就要燃尽,青烟袅袅,衬着神仙稍显惊异的眸子,我得意地笑。 哟吼,我是世界之王! 神仙抽了抽鼻子:“伸手。” 我笑嘻嘻地伸出右手。 神仙皱眉,拎起我左手:“果然。”冷哼,“我道怎么一股子血腥味。世间但凡头脑敏捷的,心智必然不坚,我还当是发现了个不世出的奇才,原来是个玩弄些旁门左道的坏才。” 我嬉皮笑脸:“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咱虽然是真小人,也不介意假借些外物。神仙大人之前也并没说不可以啊!” 神仙扔回我的爪子,轻哼:“南平,带她去吃饭吧。” 啥?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大急:“那第三关呢?” 南平碰碰我,神秘地:“先垫饱了肚子,才有的好吐啊!” 死神仙,死南平,你们真损啊!! 晚饭一过,扔给我本小册子、一根蜡烛,关进一间小房,第三关就算是齐活了。哦,还有一句“过一晚上,明天告诉我这三个人是怎么死的,对了,就算是过关了。” 哼,没错,这是一间停尸房。 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三具尸体,两男一女,恶,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皮肤都涨起来,身上斑斑点点,散发着冲天的臭气,和着房子里不知从哪飘散来的酸味,真是色香味俄,味道咱不知道,不过肯定不会好就是了都没有。 话说咱烟花地啥时候都不是个干净地儿,每个月被廉价买来的姐儿们总有那么一两个逃不脱被变态恩客虐死的命运,看得多了,对这尸首也看得淡了,只是这三位,实在是不怎么招人待见。 喉咙里直往外泛酸水儿,咽下去觉得太恶心,吐出来同样还要在这待一整晚呢,对着一滩滩那个?那不是雪上加霜么!想想都想吐……唉,恶性循环了。 深吸一口气,别过身子不看那三位,就着烛光细细看那小册子。啧啧,怎么还有残字和错字?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1] …… 册子字数不多,不过半个时辰,我便看完一遍,大抵是描述了些各种死法的表征和分辨方法,以及验尸的注意事项。 又趁着尚留有印象,抓紧再看了两遍,拍上册子,闭眼把内容过了一遍,不错,都记住了。只是连那些个残字错字都记得滚瓜烂熟呃,甚至更胜于内容,这就太夸张了吧!真是,人脑子太好使也不行啊。 抻了个懒腰,转头看向那三位,嘿嘿,打个商量,咱们两边儿都省点事,能起来告诉咱,你们到底是咋死的呗?那咱下半夜还都能睡个好觉! 正调笑地想着,只听外面传来了几声梆子,伴随着打更人一句悠长的“平安无事!”远远响起。声音被夜风拉得支离破碎地传到耳边,带出阵阵诡异。呵,刚想着下半夜,竟然就已经子时了。外面半声人响也无,只听得猫头鹰在叫,咕咕嘎嘎,松枝被夜风吹得不断摇摆,刷拉刷拉,烛火明灭摇曳,面前那女尸的睫毛似乎动了动。 我一愣,慢慢收了笑容,抬手移了下烛火,细细看那女尸,浮肿的脸青灰的皮。她的两颗上牙微有些长,磕在苍白的下唇上,印出了两点黑影,竟隐隐露出些狰狞的样子。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吹得烛火又晃了晃,那女尸睫毛又是一动,喉间好似也发出了声轻微的叹息。 唉! 这叹息悠悠响起,经久不绝,宛如一缕破败的轻纱在屋内盘桓升降,又如一只灰白的尖爪,恶意地抚弄着我的神经。 浑身的肌肉不自觉绷紧,我不住喃喃:“没有的事,我是看走眼了,那是烛火晃动,听岔了,那是窗外的猫头鹰,死人就是死人,之前见得还少么?死相比他们更惨的也不是没有,何必自己吓自己!” 只是这低语片刻之后竟也不能继续!我的喉头突然不受控制地发出格格声响,眼睛越睁越大,肌肉张紧,嘴半张,口水就快流下来了,诶诶,现在可不是什么医院能治疗白癜风复方木尼孜颗粒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ry/1153.html
- 上一篇文章: 听妈网讲故事懂爱的云朵
- 下一篇文章: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保护藏羚羊西藏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