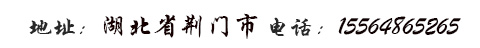云下耕首届昭明文学奖参赛作品选庭
|
庭草衔风(散文) 冉令香 一 一大玻璃杯水,黄绿色,杯底沉着一簇蒲公英,几根墨绿色叶片半悬半落。每注入开水,叶片张牙舞爪,竭力想抓住些什么。但它们什么也抓不住,一番俯仰翻腾又沉到杯底,就这样长期霸占着母亲的杯子。 有时是苦菜、白蒿、马齿苋、车前草、婆婆丁,有时是玉米须、苦瓜片、山楂干儿,它们无一遗漏,都会在母亲的水杯里轮番坐镇。似乎哪种叶子、哪种根须、哪种切片,突然某天会力挽狂澜,摇身变为调控母亲的血糖、血压、血脂指数的遥控器。我一直怀疑,这些野草能起的作用。但母亲不容质疑的神态让我对它们产生了莫名的敬畏。 此刻,母亲没有精力照料她杯子里的野草了,她静静地睡了。刚才,高吊在房顶的不锈钢输液挂钩“哗啦啦”滑过来时,刺激人的头皮一阵发紧。胶皮管儿紧扎小臂,一股消毒液喷出来直扑母亲的手背。针头穿过皮肉进入血管时,母亲的胳膊下意识颤了一下。一滴、两滴,透明的液体沿着细细的塑料管淌进针头,注入青色的血管,在母亲体内开始了漫游。 今年是第二次住院了,那么要强的母亲真的老了。护士调好输液器,白大褂旋着一股风出门。不久,凉凉的液体抚慰下,母亲竟然睡着了。母亲太累了。一头灰白的短发像经霜的顿子草铺满雪白的枕套,搭在额前的那缕白发轻轻抚着深深的皱纹。母亲轻柔的呼吸,抹平了注射时掀起的些微躁动。四周沉静成冷凝的水,压抑,让人心慌。我僵坐在木凳上不敢挪动身子,怕任何轻微的响动都能惊醒浅睡的母亲。 二甲双胍、谷维素、维生素、钙片们静躺在桌上发呆,设想着那些送服的苦水的味道。有时,看母亲把各色药片团在手心,一把吞进嘴里,用大口水送进食道,我会莫名地悲伤。母亲从四十多岁开始吃药,到现在三十余年的病史,她的胃肠道早已是药物施展手脚的道场,她的血液掺杂着药剂的溶解物运行天下,母亲那张脸上也是药物编织雕琢的纹路吗?! 二 “嗐!我这辈子,草命!”母亲疲惫地靠着床头,眼睛盯着前方出神。 “那时候啊……”顿子草、苦丁草、馍馍棵、灯笼棵……那些随风摇曳的野草听见母亲的一声叹息,“呼啦啦”全涌了出来。母亲眼睛一亮,眼角的鱼尾纹一跃一跃,游弋的小鱼一样欢畅。那一脸欢悦的神采,是那把镰刀在繁茂的野草间熠熠闪光吗?回到乡村原来如此容易。 母亲十五岁那年辍学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五个孩子同时读书。在饥饿围困的日子,一大家子忙,忙那一张张嘴,忙那一个个“咕噜噜”唱空城计的肚皮,可一天到晚还是饿。荠菜、灰菜、老虎嘴、蒲公英、马齿苋、扫帚菜、野苋菜、猪耳朵草,那些嫩芽芽刚钻出地面,一把把小铲子就挖进了竹筐。野菜粥、菜窝头、菜团子、菜豆腐,不管怎么捯饬,入嘴都是难咽的苦涩,填塞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 姥娘身体羸弱,大姨和大妗子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是首尾难顾。队伍逐年壮大的大舅一家,也在以姥爷为轴心的大家庭里摸勺子,搅饭吃。更主要的是大舅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没人照看。尽管母亲学习成绩优异,尽管十七岁的三舅高中一毕业就被推荐到水利专科学校读书,这美丽的诱惑像飘浮在家门口山头上的云朵,不切实际地招摇着她的读书梦。姥娘一句话拍板钉钉,把母亲头顶那片五彩云拍得七零八落:“女孩儿认几字就行。吃饭要紧!” 母亲没再提“上学”这两个字,一声不响挎着竹筐出门割草。 镰刀在漫山遍野的草间起落,腥咸的汗水混合着山风的吟唱装满竹筐。蚂蚱腾跃的弧线牵着走神的眼睛,蝴蝶煽动的翅膀缭乱了波荡的草浪。镰刀“嚓”地一声割破食指,血珠涌出,跌落进茂密的草丛。母亲皱皱眉,揪一把蓟菜叶,捻出浓绿的汁水涂在伤口。脊背上一凛,锥心的煞疼、火辣的灼烧感追着脉搏的跳动瞬间游遍全身每一个毛孔。她闭眼,紧按伤口,眼前光晕乱摇,两耳灌满山风,心头突突狂跳,疼痛顺着脉搏闪电般袭进脑壳。 老师几次上门劝母亲复学,但繁忙的生活重担已压住了她单薄的双肩。远远地看见老师的身影,母亲内心羞惭,悄悄躲着走了。眼见老师的背影转过石屋,母亲扛着一筐草转进家门。侄子早哭闹半天了,小脸糊成小鬼儿。裤子尿湿了,屁股咬满通红的疙瘩,他又渴又饿,张嘴老鸹似的嚎。母亲嚼一口地瓜面煎饼填进侄子的嘴巴,才慢慢止住抽噎委屈的哭声。 日出日落,月盈月亏,一把镰刀收割着微薄的希望,一只草筐装满了艰涩日子的绵长。上山锄草,下河挑水,那满山的沟沟坎坎印满了母亲的脚印,那满山的杂草灌木与母亲瘦弱的身影朝夕相处。累了,饿了,坐在地头,找一把紫黑色的野茄子填到嘴里,眼睛却盯着脚边的野草出神,割断的刀口上正涌出乳白色的汁液,泪珠一样颤巍巍地敷在伤口。一阵风吹,一阵日晒,汁液在伤口凝固成粘稠的黄褐色米珠。几天后,刀口下的叶腋又钻出新芽,割过的草地又萌生出绿油油的一片。看看满手黏糊糊的黄绿色草汁,就着刺鼻的苦涩味咀嚼几颗野茄子,一棵草受伤、自愈、生长,自我保护的机智,瞬间触动了母亲。 草命!看看田间地头的野草,风风雨雨,泼泼辣辣一茬茬辗转轮回,从容与时光进行较量。母亲15岁那年认命了。被生活反复淘洗的日子久了,谁不是认命呢? 三 那年春天,我头一次见母亲熬草药。 从邻家借来的黑砂锅蹲在小泥灶上,里面装满清水浸泡过的草药。几根木柴燃起一团莹莹的火,幽幽地舔舐着黑漆漆的砂锅底。锅内的热气丝缕团揉地起身,汤药绽开细细的浪花时,母亲拿竹筷轻轻翻搅一下,用筷子撑起锅盖,苦涩的药味立刻跟着风窜满院子,翻过墙头,钻进胡同,飘满整条街,到处流散一个受伤者的痛楚。 父亲驾驶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石头,开出石料厂不远,拖拉机突然失控,像脱缰的野马从山坡俯冲而下。路人惊叫着四散奔逃。情急慌乱之中,父亲纵身跃出驾驶座。一声惊天巨响,载重两吨半的拖拉机翻在山脚,后轮残忍地碾过了他的右脚。当即,鲜血迸流,人高马大的父亲僵挺着血肉模糊的脚,痛苦地抽搐成一团。身下不堪重负的野草,枝断叶残,也是满身伤。 憨厚的父亲只不过想多拉快跑,多挣几个工分,早日把负荷沉重的家庭拖出生活的低谷。当第一辆拖拉机开进村时,他果断地甩掉了肩头的黑马鬃车襻,以为再也不用拉着地排车或推着独轮车,垂头抵肩崩腰,斗牛似的向山坡上拱。当拖拉机像小山一样悲壮地翻倒时,他脚上奔涌而出的血染红了大片靑油油的野草,他这座铁塔轰然跌下山脚。 那两吨半石料压断的野草,经过一场雨、几场风,又挣扎着钻出新芽,窜高,拔节,抽穗,呈现繁衍后代的预兆。而石膏、绷带、木板,捆绑治疗了三个多月的父亲,竟不如一棵草自愈的速度,只能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唉声叹气。血液回流不好,整条小腿都发酵似的涨疼。母亲把熬好的汤药倒进脸盆,再用浸透草药的毛巾,一遍一遍给父亲骨折的脚、肿胀的腿热敷,消炎,消肿,活血。足有半年,家里天天草药味弥漫,与那一院子压抑、忧郁和伤痛纠结缠绕。那一层疗伤的膜,在草药的抚慰下艰难新生。 药锅蹲在土灶上“咕咕”冒泡,那一院子乱窜的药味多像痛苦的呻吟和祈祷?! 一遍、两遍、三遍。三遍细火慢熬,一锅药最终才熬成一碗汤。想想这些草药经过采挖、晾晒、剪切、烘焙、翻炒等工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得道成药。那么,熬药自然也性急不得,需用文火轻拢慢捻抹复挑,才能把草药那颗苦涩的心慢慢打开,把尘封已久的沧桑一丝一缕地释放出来。熬,不就是生活的修炼吗? 过日子就是熬,父亲的脚还没好利索,爷爷却被繁重的日子熬倒了。干了一辈子活,吃了那么多苦,却因吞咽困难,病得只剩下枯瘦的骨架。 身材高大的爷爷,力壮如牛,走路生风,怎能生病呢?大清早,朝阳刚跳出东方的地平线,爷爷已风风火火,推着一车子草从野外回到牛栏院。再一气儿挑二十多担水饮牛,那一路淋淋漓漓的的水滴,坠着水桶跌落,硬邦邦的土路像下过小雨似的濡湿,软了心肠;夜幕织一层纱网,笼住村里的树梢屋脊,悄然滑落地面时,牛栏院里那盏提灯跳跃着豆大的火苗,映着一米多长的铡刀寒光闪闪。一捆新鲜的青草塞进铡口,爷爷猫腰,双手按着铡刀把,“吁嚓、吁嚓”铡草的声音与牛马反刍咀嚼的浑声,合奏成乡村独特的小夜曲。早春的风忽冷忽热,哈口气化开了厚厚的冰盖。爷爷甩开膀子开荒整地,大镢头起起落落呼风唤雨,酥软的泥土翻开身子喘息透气。暖烘烘的太阳粒子撒欢儿,在团团丛生的茅草间钻进钻出。爷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侍弄庄稼。他弓腿弯腰锄草间苗,满脸的汗珠“噗噜噜”滚落,砸得幼苗颤巍巍抖身,狡猾的野草却与风嬉戏,笑得东倒西歪;他虔诚地单腿跪地,薅除混杂在苗间的狗尾草;他坐在地头抽袋烟歇息,也会顺势拔掉地头的野草……一年四季,早出晚归,爷爷撂下锄镰镢锨,就是扁担水桶、手推车,哪见过他清闲得手指溜风呢?他哪有时间生病呢? 爷爷病倒了,母亲默默地支起黑砂锅,又在土灶上开始了煎熬。 小时候,每见路边的药渣,我总心慌害怕。黑沉沉的夜,一弯冷月斜挂树梢。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冷不防一滩散碎的药渣拦在眼前,近看,还散着炉火的余温和清苦气息。一阵惶惑倏然从心底泛起,我似乎看到一张憋得通红的脸,强忍咳喘,灌下一碗黑乎乎的药汤。 暗淡的灯影下,爷爷面色萎黄。他端起浓浓的药汤,长吸口气,嘴唇贴着碗边一气儿喝下半碗,眉头立刻耸成山。略一犹豫,他深吸一口气,又喝干剩下的半碗,擦擦嘴角,重重把碗撂在桌上,似乎完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天天喝汤药的爷爷,并非都这么顺利。他大发脾气的时候,那碗汤药放凉了也喝不进嘴里。如果他焦躁地拾起碗扔到门外,那是因吞咽困难,痛苦难耐。 母亲用厚毛巾包住滚烫的药锅把手,趁夜黑无人,端到路口倒掉,嘴里默默念叨:“药到病除”。尽管,我和父亲、姐姐、弟弟,也像母亲那样虔诚地把药渣倒在大路边、胡同口,但爷爷的病情并没有像我们全家祈祷的那样好转。他在野草最繁茂的夏季,走了。 爷爷与草争斗了一辈子,最后融进了泥土,却与草贴得最紧密。山风浩荡,草浪涌动,那是爷爷与草坦诚而热烈的交谈吗? 每年清明,父母都要来爷爷的坟头拔除草芽,培层新土,给爷爷敬一壶老酒。每年下元节,父母也来爷爷的坟头薅掉结籽的衰草,培层新土,敬一壶老酒。爷爷坟头的草年年拔,年年照样绿。三十余年倏忽而去,爷爷生前居住的老宅早已坍塌。爷爷的窗前,白蒿、婆婆丁、车前草、苦菜、马齿苋等诸多野草却萌生满了院子。 风过,草吟,大地上的一切,谁能长得过草呢?岁月轮回,唯有野草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准时恭候春天。 四 是从父亲受伤未愈,爷爷去世那年开始吗?母亲喝水的碗里也多了几样东西:白蒿、苦菜、婆婆丁、马齿苋、车前草。 母亲被沉重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了。家里、医院两头跑。炊煮洗刷、缝补浆洗,除了忙活一日三餐还要下地干活。繁琐沉重的家庭开销,四个孩子的读书费用紧箍咒一样在头上紧了一圈又一圈。 那个傍晚,母亲还未赶进家门就听到母猪抵着圈门狂叫。一天了,空荡的院子里,它一直在敏感地捕捉母亲的脚步声,却只有无聊的麻雀扑棱棱在树杈间起起落落。它饿了,在猪圈焦躁地转圈,顶着木门“哐哐哐”乱响。早已宿窝的鸡们受到惊扰,“叽叽”乱叫。警觉的黑狗四肢撑开,肚皮贴地,耳朵直挺,眼珠“咕噜噜”旋转,警惕地守着猪圈。间或一两声短促的吠叫,警告圈里那个莽撞的家伙。难道母猪也知道自己在家里的重要地位?一年两窝猪仔,母亲拿它当最疼爱的孩子精心伺候。母亲进门,来不及喘息,慌忙给母猪备好食,倒进猪食槽。母猪撒欢儿地“歘歘歘”地大嚼时,母亲竟然靠着石墙睡着了。 风拂草动,一撮墙头草撩着母亲的脸一阵酥痒,猛然醒来。 寒冬腊月,越近天黑,朔风越紧,刮擦着老树的枯干嗡声怒吼。临产的母猪躁动不安,出出进进,衔草垫窝。狂风卷着零散的雪花落地时,母猪终于在暖窝躺下。母亲把木柴架好,燃起,红红的火光瞬间撵走了猪圈里的寒气。黑沉沉的夜色在周围跳动,母亲拨弄着旺旺的火堆,轻轻捋着母猪粗糙的脊背,安抚慌乱的母猪。“咯吱”、“咯吱”树枝在雪的重压下呻吟断裂时,第一只猪仔来到了人间。剪断脐带,把猪仔放进温暖柔软的麦草窝,它跌跌撞撞,试探着站起来。 天光放亮时,风静雪停,天地间一片混沌的白。一盆热乎乎的小米黄豆汤下肚后,母猪躺在暖草窝安然享受着母子温情,八只猪仔趴正在怀里闭眼吮吸。 母亲一夜未睡,看看麦草窝里叽叽歪歪的猪仔,柔柔被雪刺痛的眼,活动活动僵硬的膝盖,想站起来时却一屁股跌坐在雪地里。她的手脚冻僵,她全身的骨头散架似的筛糠颤抖。幸亏身旁的草堆,抱住了疲惫不堪的母亲。 朝阳红着脸儿升起来了,一缕缕炊烟手牵手爬上湛蓝的天野。墙外孩子嬉闹打雪仗的声音震得落雪纷纷,唤起母亲的斗志。她拍打、按揉一统腿脚,扶着石墙慢慢站起。去学校早读的孩子就要回家吃早饭了!麦草燃起的火苗“噼啪”舔舐着锅底,映红了母亲憔悴的脸,柴草燃烧的焦香引起她肚腹一阵阵空鸣。 草以生命的另一种姿态,奔放腾跃,温暖了一个积雪掩盖的庭院。 那个秋天,瘦弱的母亲突然满脸虚肿。她烧水的方式突然大变,抓一把晒干的白蒿或婆婆丁洗净,烧至水开,凉在小瓷盆,大碗大碗地连喝一天,仍然口干。 天热汗多,缺水吧。母亲顾不上多想,天蒙蒙亮,背起水壶,又下地干活了。绵长的秋天,庄稼排队成熟的日子就是一场马拉松赛跑。 “起床做好饭,送到地里。”母亲出门前的嘱咐,并未把我从沉睡的梦境叫醒。我正陷在长长的玉米地,四周雾气蒙蒙,没有人声,连黑老鸹的鸣叫也听不到。一穗穗粗长的玉米甩着满嘴胡须,围着我旋转成风火轮。我眼花缭乱,想纵身跃出圈子,却又渴又饿浑身乏力,被濡湿的玉米须紧紧缠绕,挣扎不得。眼见父母拉着满满一地排车玉米,像踩在棉花包上一寸一寸地挪,我却不能跑过去推一把。突然,头顶明晃晃的太阳一闪,瞬间乾坤颠倒,我又坠入无底洞。我惊恐地大喊大叫,拼命要抓住些什么,脚下一绊,一头扑倒。我想站起身逃跑,蛮长的地瓜秧错杂纠缠,我的脚怎么也拔不出。不远处的母亲正猫腰礤地瓜,雪白的地瓜片“唰唰唰”飞出擦板,脚边转眼就是一堆。忙活的母亲听见我的呼唤,慢慢转过身,却被周围白花花的地瓜片包围着,簇拥着,迈不动步子。又一个明晃晃的光圈闪过,母亲突然扑倒在地…… “哐啷”,木板门猛然大开,掀翻了我的梦。父亲心急火燎推着小车闯进家门,正礤地瓜的母亲突然晕倒。那天,从医院回来,母亲吃饭之前就增加了一道程序:从白色的塑料药板里,抠出一片二甲双胍,一口水送进肚。 “二甲双胍片,适用于单纯饮食控制及体育锻炼治疗无效的2型糖尿病。”我反复端详着药盒上的黑色小字,心里一阵酸楚。母亲从小吃苦受累,还没享受过安闲富足的日子,竟得了这种“富贵病”?! “嗐!草命!”母亲洗一把玉米须放进水壶熬煮,炉火跳跃的红光映着她虚肿的脸。刚读护理专业的姐姐稍微一摁,母亲脸上陷下一个坑窝,再按她的手脚也是坑窝。读初中的我和大弟、读小学的小弟,高深莫测地看着姐姐的一行一动,揣测母亲的病情轻重,对于未知命运的惶恐统摄了这个艰难的家庭。 泼辣的母亲从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在供孩子读书的最艰难的年月,饥饿、疲乏无力的困扰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纠结的矛盾,母亲根本无法摆脱。血糖指数就像隐形的魔掌紧紧卡着母亲的脖子。随着年岁延长,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每次住院,药用剂量都会增长。吃饭成了母亲面对的最大难题。当她不得不谨慎筛选着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含量或高或低的食物,按量定餐时,野菜成了她饭碗和水杯里的主角。 母亲从未放弃,那只大玻璃杯常年与野草为伍。任何道听途说的降压降糖降脂的偏方、秘方,都能绊住她匆忙的脚步,让她纫进耳朵细听谨记,然后到山坡野地四处搜寻,回家后如法炮制。 几天忙碌之后,母亲虔诚地把一撮野菜放进玻璃杯。滚开的水倒进去,野菜翻滚起伏,肆意绽放,水眨眼变成黄绿色。待水温不冷不烫时,母亲“咕咚、咕咚”坚决地连喝几大口咽下,嘴唇紧闭,怕苦涩的气味窜出嗓子眼儿,嘴角却有一丝灰绿色的水渗出。手背抹一把嘴角,母亲转身又忙成旋转的陀螺。忙活过半天,口渴时,又是几口果断的吞咽。 五 清炒绿豆芽、辣子鸡块、清蒸鲳鱼、白菜小豆腐,青红绿白,四盘菜像四个懂事的孩子乖乖摆在小圆桌上。我提着一箱无糖牛奶进门时,母亲面前的小碟里两块鸡肉、一条小鲳鱼,她正满足地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慢慢咀嚼,享受食物赐予的幸福。 我的鼻子一阵酸涩,每天依靠各色药片和胰岛素调节内分泌均衡的母亲,两口荤腥就心满意足了。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母亲从不让为她过生日。“忘生(旺盛),忘生(旺盛)。”这是她的借口吧,年年给父亲过寿,她也就陪着一起过了。 “我一个人吃苦,全家人都好好的,就够了。”母亲的自我排解有些悲壮,有些凄凉。我眼眶一热,眼泪几乎涌出来,赶紧转过身为自己也泡了一杯白蒿水。 白蒿在杯中翻腾,起浮,静止在杯口时,水转变成了黄绿色。我捧起水杯,慢慢喝几口。清苦的滋味融有轻微的土腥味,顺着食管,进入胃囊,渗入血液,刺激人的精神一振,那是任何甜美的饮品都难以捕捉的感觉。 我也开始晒白蒿、婆婆丁、车前草了。 捧书静读时,洗净一撮婆婆丁放进杯子,倒入滚开的水。杯底的婆婆丁辗转翻腾,扯着我的头皮一紧一疼。滚水与婆婆丁的交锋凌厉而急遽,几次急流激荡的较量,僵硬纠缠在一起的婆婆丁渐渐软化,膨胀,与水融为宁静和谐的画面。 草青涩的滋味越来越寡淡,水也呈浅淡透明的灰绿色时,不管怎么摇动,草只会随形符合晃晃叶片,那么温顺敦厚,甚至有些疲惫,让人疼惜。那草宛如一颗被生活驯服的心,静如止水,却宽厚大度,包容一切。一块反复淘洗的棉布,迎着阳光扯起,千疮百孔的纤维间透过的刺眼光线,情不自禁让人潸然泪下。 昭明文学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mazhuia.com/ymztx/2652.html
- 上一篇文章: 院刊推介陈晓伟马负文豹与草原游
- 下一篇文章: 奇迹穹窿山惊现特大号野生灵芝,品相完